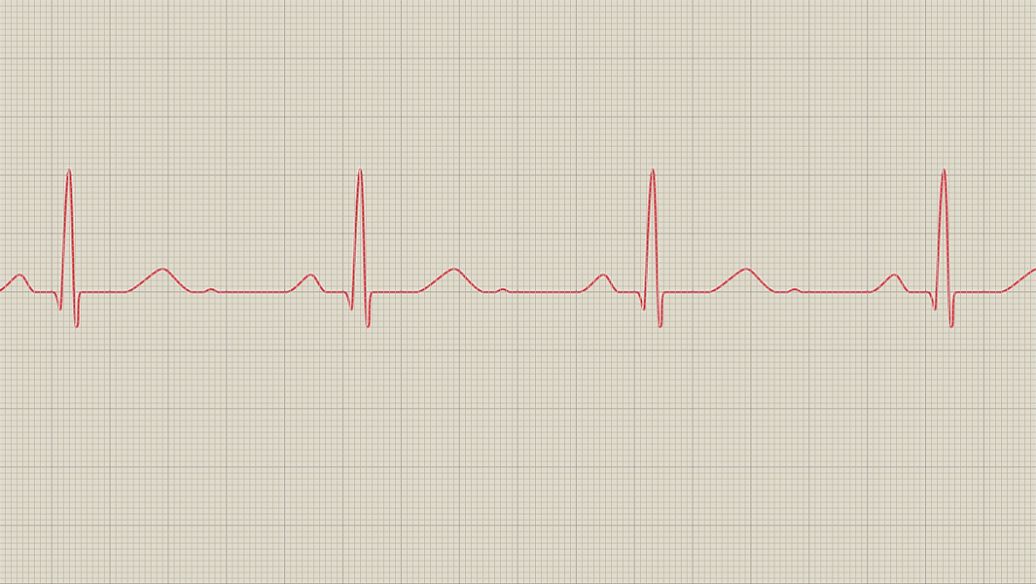入胥梦吧 关注:27贴子:2,068
- 5回复贴,共1页
-
二月已破三月来。昨晌嘈嘈切切雨过,尘埃涤尽,明空澄澈,霁光倾倒千里彤云。我一闲身,前面几个阿兄撑着,也鲜有俗事绊人。近来我却忧甚,饭不思,夜不寐,心也沉沉。
我……为新茶劳神。
我迩日偏好的四季春,库存告罄。其出自台地,京中不多见,有也是陈茶。裴家的商铺才运货上京不久,下一次不知杳杳何期。只一位在城外结庐而居的友人,前些日子才得了些。便决意厚着脸皮蹭他一蹭。
是以,翌日的一早,便驱车赶往京郊。我知其不好说话,又因着那文人相轻,便是场恶战。故让随行小僮携着一应茶具,在陶然亭附近寻个地儿,教那柴禾活火先沸茶铛,待试新茶。
好说歹说,腆着脸终是谈妥,意满而自得,便寻小僮。
抱着茶罐一路行来,途经之处,所观是众相千百。人一活得疲了,或剔于锱铢,或溺于声色。还不如戴斗笠,披蓑衣,做个芦人渔子亦超然。可寻常布衣需为了生计奔波,赀储钱财。倒真是三界如火宅,众生皆苦,各有各难处。
忽的驻足,一眼望去。亭内有窈窕,身影绰约,谙熟得像我画过千万遍的写意山水。
我……却不知如何相认,非是不愿,而是不敢。青衫踯躅。
默了一瞬,万念俱寂,定心往前。我怕贸贸然出声儿惊住她,大致行到她的视野内,方掷出一句。
“可是温都姑娘?”
二月已破三月来。昨晌嘈嘈切切雨过,尘埃涤尽,明空澄澈,霁光倾倒千里彤云。我一闲身,前面几个阿兄撑着,也鲜有俗事绊人。近来我却忧甚,饭不思,夜不寐,心也沉沉。
我……为新茶劳神。
我迩日偏好的四季春,库存告罄。其出自台地,京中不多见,有也是陈茶。裴家的商铺才运货上京不久,下一次不知杳杳何期。只一位在城外结庐而居的友人,前些日子才得了些。便决意厚着脸皮蹭他一蹭。
是以,翌日的一早,便驱车赶往京郊。我知其不好说话,又因着那文人相轻,便是场恶战。故让随行小僮携着一应茶具,在陶然亭附近寻个地儿,教那柴禾活火先沸茶铛,待试新茶。
好说歹说,腆着脸终是谈妥,意满而自得,便寻小僮。
抱着茶罐一路行来,途经之处,所观是众相千百。人一活得疲了,或剔于锱铢,或溺于声色。还不如戴斗笠,披蓑衣,做个芦人渔子亦超然。可寻常布衣需为了生计奔波,赀储钱财。倒真是三界如火宅,众生皆苦,各有各难处。
忽的驻足,一眼望去。亭内有窈窕,身影绰约,谙熟得像我画过千万遍的写意山水。
我……却不知如何相认,非是不愿,而是不敢。青衫踯躅。
默了一瞬,万念俱寂,定心往前。我怕贸贸然出声儿惊住她,大致行到她的视野内,方掷出一句。
“可是温都姑娘?”
-
草树荣深,经眼的春葩也惹不去我的注目,我只和悦地看向她。
“又是一年寻芳挼红,忽有故人眼前过,某便上前一探。”
她其实算不得故人,仅惊鸿一面又匆匆一瞥,但在我心里,她着实是比故人还具象化的存在——她同草色,遥看有近却无,是我捉摸不了的。
“确然巧,尽是在三春里遇见。某有疑——姑娘莫不是句芒座下的神女?”
我没有闺阁的那么多顾忌,便隔着千山更万水中跃过的白驹,将两年前来不及告知于她的,倾囊相语。
"在下裴和光,姑娘亦可唤乐只。"
微不可察地涩笑,话轻得如霁风,蹑口而出便可弥散似的。
“我原以为,蓟门的那年春,除却花开不是真。”
怀煦而拜。既是拜她,也是拜这无边韶光、排叠花枝。
“幸逢东君开我眼,得以识卿面。”
草树荣深,经眼的春葩也惹不去我的注目,我只和悦地看向她。
“又是一年寻芳挼红,忽有故人眼前过,某便上前一探。”
她其实算不得故人,仅惊鸿一面又匆匆一瞥,但在我心里,她着实是比故人还具象化的存在——她同草色,遥看有近却无,是我捉摸不了的。
“确然巧,尽是在三春里遇见。某有疑——姑娘莫不是句芒座下的神女?”
我没有闺阁的那么多顾忌,便隔着千山更万水中跃过的白驹,将两年前来不及告知于她的,倾囊相语。
"在下裴和光,姑娘亦可唤乐只。"
微不可察地涩笑,话轻得如霁风,蹑口而出便可弥散似的。
“我原以为,蓟门的那年春,除却花开不是真。”
怀煦而拜。既是拜她,也是拜这无边韶光、排叠花枝。
“幸逢东君开我眼,得以识卿面。”
【增添版!】
-
“东君总归是圆滑的,八面玲珑地解决瑞雪与新绿的争辩,也长袖善舞地送走积年乱麻,赠世人以希冀。”
温言悦语间,我掀袍在她对面落座。酡云哺着晴空,不时有和风缱绻周遭。
她被名为世家的器,慢煲细煨十余载。一姿一态,譬比仕女图上的剪影。她令我想起母亲屋中冰湃水果的钧窑青瓷,似玉似镜,盘底蔓延着折枝的桃花纹路。一盛水,就如山桃扣着春溪渌渌。谧极,雅致,入画也自成风骨难拓。
——她不用开口言谈什么,我便甘为平子三倒。
恰在此时,我本要寻的小僮先于我寻到此处。我将茶罐递予他,看着他前去准备的身影,蔼蔼晏晏出声。
“不知姑娘可否赏脸吃个茶?”
溶光相照,我沦入遐思。哪怕偏坐一隅,我也能眺望及远处的山长水阔。春情何多,一霎好风便可叠起几幕翠绿,却亦会攒走落红。我无可奈何,却又生出侥幸与欢欣。幸而,共我赏花人还在。
我情不自禁地碰了碰腰间缀着的绣囊,方觉安心。
-
“东君总归是圆滑的,八面玲珑地解决瑞雪与新绿的争辩,也长袖善舞地送走积年乱麻,赠世人以希冀。”
温言悦语间,我掀袍在她对面落座。酡云哺着晴空,不时有和风缱绻周遭。
她被名为世家的器,慢煲细煨十余载。一姿一态,譬比仕女图上的剪影。她令我想起母亲屋中冰湃水果的钧窑青瓷,似玉似镜,盘底蔓延着折枝的桃花纹路。一盛水,就如山桃扣着春溪渌渌。谧极,雅致,入画也自成风骨难拓。
——她不用开口言谈什么,我便甘为平子三倒。
恰在此时,我本要寻的小僮先于我寻到此处。我将茶罐递予他,看着他前去准备的身影,蔼蔼晏晏出声。
“不知姑娘可否赏脸吃个茶?”
溶光相照,我沦入遐思。哪怕偏坐一隅,我也能眺望及远处的山长水阔。春情何多,一霎好风便可叠起几幕翠绿,却亦会攒走落红。我无可奈何,却又生出侥幸与欢欣。幸而,共我赏花人还在。
我情不自禁地碰了碰腰间缀着的绣囊,方觉安心。
扫二维码下载贴吧客户端
下载贴吧APP
看高清直播、视频!
看高清直播、视频!
贴吧热议榜
- 1五一请你来这里2671830
- 2S1世界赛冠军上单Shushei去世2368981
- 3李铁二审获刑20年1825880
- 4如何评价最近的“无敌莽夫”论战1623213
- 5斯诺克世锦赛赵心童火力全开1389752
- 6董袭莹论文被撤下谁在背后发力1279125
- 7沃尔玛通知中国供应行发货1249536
- 8屠呦呦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920874
- 9阿森纳0-1巴黎圣日耳曼810920
- 10饿了么加入外卖大战716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