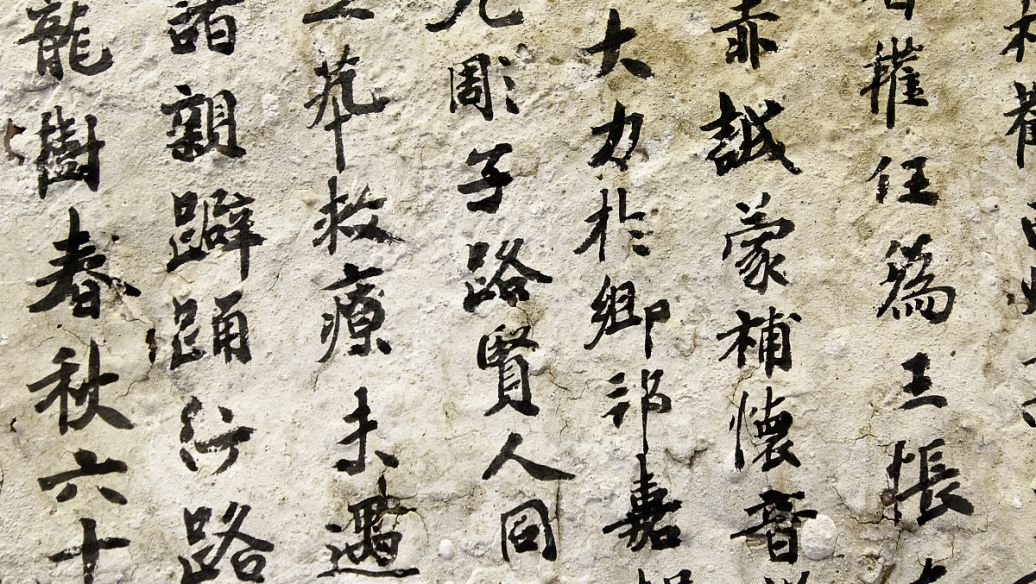在下并无能力在现在用几段话说清这两个问题,也暂时不打算写论文,只是考虑到若在下要更进一步去看,方向在何处。
有两个地方,在下每常考虑。
一、朱子认可虎狼之仁、蜂蚁之义,獭之知礼、乌鸦之孝,且称物却专,而人易昏,即不是“移情”,而是实然。此处牟教授及一部分学者将认为朱子这样做,是道德义减杀。而朱子学中,“善”、“是”一原,至善天理切实地为物性,为事理,这使得“由仁义行”不经任何周折,便必然当即尽事物之理(牟教授认为不归属于性理者)。
二、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的时候,牟教授会认为,在实然层面,这是德福不一致的,但圣心可超化之。而朱子必定认为,以圣人所行,位禄名寿等等作为当然而然,其可能性全具,其趋势不容已。桓魁是确实地不能如圣人何。由于在两种学问中“气化”的不同意义(是天地浩浩人在其中还是仅是补充助缘),朱子以为刚健者,牟教授或以为悲壮。
至于闻见之知被带出,还是要回到朱子认为事物之理切实是性理,天地万事万物在某个确定意义上都可以讨论善不善,当然不当然,仁义不仁义上。天下所有的“然”(人能闻见思议者),不论其是否当然,都是当然之理的或直一或曲折的彰显。格物格当然,当然之则不彰于虚空,弄清其“文理密察”,必由万殊中见。如真知孝,必於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中孝心如何显现,这其中,自然也涉及对凉席、扇子、棉被等等的了解,惟皆作为当然之则彰显所透过的途辙,被格当然所带出。价值根据在事实之先,对于价值的判断,却在对于事实的真判断之后。
有两个地方,在下每常考虑。
一、朱子认可虎狼之仁、蜂蚁之义,獭之知礼、乌鸦之孝,且称物却专,而人易昏,即不是“移情”,而是实然。此处牟教授及一部分学者将认为朱子这样做,是道德义减杀。而朱子学中,“善”、“是”一原,至善天理切实地为物性,为事理,这使得“由仁义行”不经任何周折,便必然当即尽事物之理(牟教授认为不归属于性理者)。
二、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的时候,牟教授会认为,在实然层面,这是德福不一致的,但圣心可超化之。而朱子必定认为,以圣人所行,位禄名寿等等作为当然而然,其可能性全具,其趋势不容已。桓魁是确实地不能如圣人何。由于在两种学问中“气化”的不同意义(是天地浩浩人在其中还是仅是补充助缘),朱子以为刚健者,牟教授或以为悲壮。
至于闻见之知被带出,还是要回到朱子认为事物之理切实是性理,天地万事万物在某个确定意义上都可以讨论善不善,当然不当然,仁义不仁义上。天下所有的“然”(人能闻见思议者),不论其是否当然,都是当然之理的或直一或曲折的彰显。格物格当然,当然之则不彰于虚空,弄清其“文理密察”,必由万殊中见。如真知孝,必於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中孝心如何显现,这其中,自然也涉及对凉席、扇子、棉被等等的了解,惟皆作为当然之则彰显所透过的途辙,被格当然所带出。价值根据在事实之先,对于价值的判断,却在对于事实的真判断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