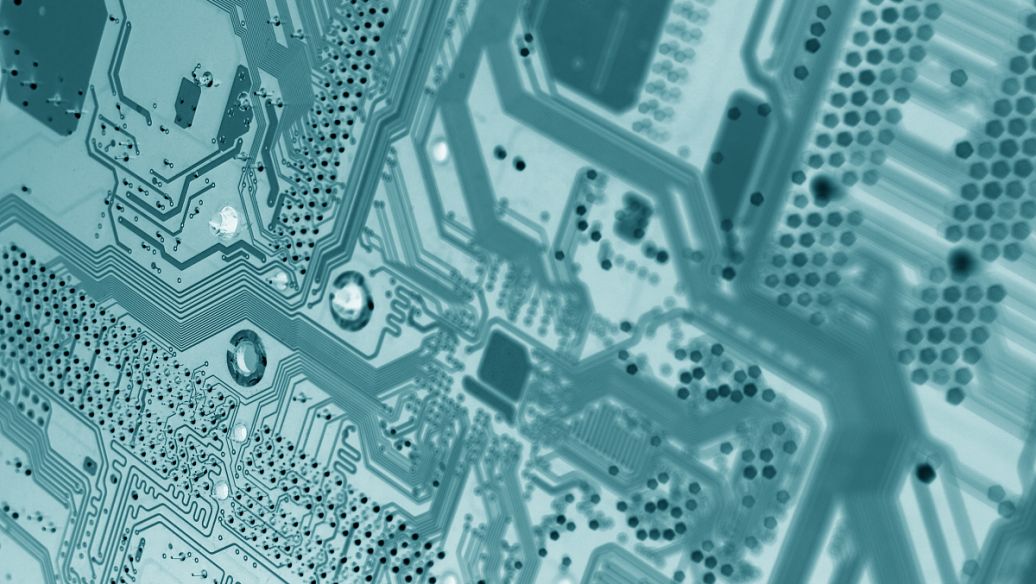“……”黄锐深呼吸,继续撑着笑,而眼前两人突然在小区门口
停住,小区有些破旧,墙皮漆着一圈因阴雨的黑痕,成为一条岁月难以抹平的疤痕,底下开张一家杂货铺,悬着褪成姜黄色的竹帘,百应俱全,门口的架子堆砌摆放着泛黄的海报、书籍、漫画,黄桷树的绿影从高处悬落在书架上面,风吹便动,如同是织出一张绿茵茵的树网。
再往里走,巷口传来自行车铃铛声,后座绑着冰糕箱的小贩正吆喝“绿豆冰棍”,小区里不知道是谁家的收音机播放咿咿呀呀的川剧,同时一股油辣子的辛香四面八方地包裹而来。
原来是到家了。
姥爷从兜里摸索出一大串钥匙,一个个捻过去,最终找出一条黄皮钥匙,插入锁孔里。沈邃换下鞋子一言不发地走进屋子里,姥爷回头打量了黄锐几眼,想来这人跟他们一路,满头大汗,要说是骗子,也太折腾自己,便还是招手让他进来了。
停住,小区有些破旧,墙皮漆着一圈因阴雨的黑痕,成为一条岁月难以抹平的疤痕,底下开张一家杂货铺,悬着褪成姜黄色的竹帘,百应俱全,门口的架子堆砌摆放着泛黄的海报、书籍、漫画,黄桷树的绿影从高处悬落在书架上面,风吹便动,如同是织出一张绿茵茵的树网。
再往里走,巷口传来自行车铃铛声,后座绑着冰糕箱的小贩正吆喝“绿豆冰棍”,小区里不知道是谁家的收音机播放咿咿呀呀的川剧,同时一股油辣子的辛香四面八方地包裹而来。
原来是到家了。
姥爷从兜里摸索出一大串钥匙,一个个捻过去,最终找出一条黄皮钥匙,插入锁孔里。沈邃换下鞋子一言不发地走进屋子里,姥爷回头打量了黄锐几眼,想来这人跟他们一路,满头大汗,要说是骗子,也太折腾自己,便还是招手让他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