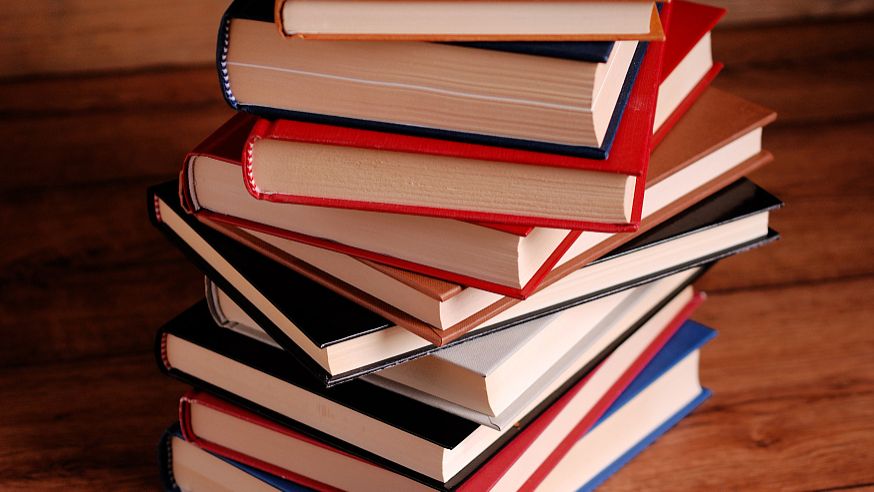在柳祉只有七岁时,风很凉的一个夜,普陵江水裹挟着上游带来的泥沙,周遭灯火次第亮起,星星点点落在水中,被波纹揉皱成细碎的萤火。恍惚听见江水在暗处低吟,如老者絮语,讲述着千年来溺亡的月光与未寄出的信笺。
柳祉亲眼目睹了母亲将出生不到三天的婴儿丢入江中,滚滚江水泯灭了他的亲弟弟。
这个女人无人陪产,也未坐月子,生完孩子便匆匆搭乘直通镇上的公交车回家,不许人靠近,也不与人交谈,无人知晓她为什么做出如此残忍之事。
柳祉清楚,父母的婚姻无异于地下腐烂的树根,长不出繁茂的绿叶 ,自己不过是性的果实,偏是这棵烂果,让人误以为这棵树还未死去,年复一年地苟延残喘。
他只是静静地望着母亲癫狂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拱桥的尽头。柳祉没有追赶,震惊、悲伤、恐惧与迷茫像无形的绳索,紧紧束缚住了他的手脚。
他本该没有弟弟的,可偏偏在桥旁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啼哭。或许是出于对生命的怜悯,他蹲下身,凝视着这个被遗弃的婴儿。婴儿的皮肤透红,还有些皱巴巴的,柳祉从未见过自己那被丢进江里的弟弟的模样,但此刻,他想着,弟弟大概也是这样的吧。
柳祉没有停留太久。他站起身,冷风风打过他额前凌乱的发丝,吹得他眼中的泪水在稚嫩的脸庞上打了个转,最终悄然坠入江水之中。
远处的寥寥灯火明暗变换,普陵江中的神仙今夜格外贪婪。
家中的木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像是无休止的呻吟。床上的婴儿已经安然入睡。
柳祉有着菩萨般的心肠,救下了这个本该在寒风中或江水中消逝的生命;但他又仿佛是个十足的恶人,自私地将另一个生命拉入了这无尽的深渊。
当夜,那个双眼布满血丝、精神亢奋的男人回来了。他醉醺醺地沉浸在红红的票子中,得知自己的女人扔下孩子跑了后,只是嚷嚷着等赢了大钱要给柳祉找个“胸大腰细屁股圆”的小妈,嘴里还嘟囔着一些**什么的话。还抽出五十块钱,打发柳祉去买些好菜。
柳祉住在普陵江下游的小镇上。他借着月色,在走几步就到头、坑坑洼洼的砖路上,买了一些现成的猪杂碎——这类菜看起来分量不少,却花不了多少钱。剩下的钱,他悄悄塞进裤腰里,用布条腰带紧紧勒住,只将几块钱交给了那个男人。男人似乎真的在牌桌上赢了不少,没再细算,随手将钱塞进了口袋。
那一夜过后,断陵桥旁的弃婴成了他正式的弟弟。柳祉在用来糊柜子的乱七八糟的报纸和杂志上踮着脚找了半天,最终选了一个单字——“钰”。这个字既有“金”,又有“玉”,将来的小孩一定能温润如玉,富贵安康。
所以他的弟弟名叫柳钰。
他用偷偷留下的钱买了几包散装的奶粉,和在米汤里喂给柳钰。
那个年头,这边的城市经济萧条,更别提这了小村镇,一家里能出个工人每月赚个几百块日子过的都算滋润。自从有人走歪路子赚了钱,这一片的风气就如同集市上的臭鱼,腥臭糜烂。
宁安镇如今邻里之间都不走动,人情淡漠,有几家做起了违法买卖,这个当上了地头蛇,那个打家劫舍进了局子,柳祉家老爹不争气又不老实,正经过日子的人家不敢接济,道上的又没人看的起,人人自危的时候,日子过得一直很紧巴。
在柳祉出生前些年,困难到易子而食的家庭也是有的,小时候母亲最常念叨的就是说柳祉生在了好时候,可不知什么时候这句话就再也没从她嘴里说出来过。
柳钰的奶粉就算再怎么省着喝,也撑不了几天了。米汤根本不顶饿,孩子饿得哭得脸发紫,没什么肉感小手因长时间的哭泣而僵硬发麻。
将败的落日透过木框的玻璃窗,斜斜地洒在两个孩子的身上。一个费力地摇着啦另一个,哭声渐渐减弱后,他才半跪在床边,轻轻搓开婴儿那因哭泣而僵硬的小手,低声呢喃:
“哥哥不会再让你挨饿。”
一个孩童的眼中竟透出令人生畏的坚定。那未经世事的心里,刻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责任——照顾好弟弟。他恨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恨自己太小,无法为弟弟撑起一把伞。
第二天,他勉强让弟弟的肚子填饱后,便抱着孩子去了镇边的“献”血车。一只手紧紧搂着弟弟,另一只手的血液缓缓流出。他抽了三次血,才勉强凑够200毫升。
三个针孔,200毫升血,换来82块钱,足够柳钰喝上半个月的奶粉。在柳祉看来,这是一笔值得的交易。
他那小小的脑袋里只知道,血很值钱,能救弟弟的命。然而,那又粗又长的抽血针,却在柳祉的心脏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红痕,成为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伤痛。
出了献血车几步柳祉就倒在了镇边的桥洞上,不知多久,幼儿的哭声将他叫醒,他睁眼就是黑洞洞的一片,侧头剪见一个约莫四五十岁的男人怀里抱着柳钰,生疏的摇着孩子。
柳钰用手撑地强爬起来,警戒的盯着男人,如一只蓄势待发的小兽,男人也察觉到柳祉的敌意,努了努嘴,把哇哇哭的娃娃递给了柳祉。
“孩子好像饿了。”
“刚弄到钱,还没买奶粉呢。”
空气静了一瞬间,只剩下娃娃的哭声,男人向桥洞的一边望了望,又扫柳祉一眼,他在这待这么久,心下已经了然。
柳祉亲眼目睹了母亲将出生不到三天的婴儿丢入江中,滚滚江水泯灭了他的亲弟弟。
这个女人无人陪产,也未坐月子,生完孩子便匆匆搭乘直通镇上的公交车回家,不许人靠近,也不与人交谈,无人知晓她为什么做出如此残忍之事。
柳祉清楚,父母的婚姻无异于地下腐烂的树根,长不出繁茂的绿叶 ,自己不过是性的果实,偏是这棵烂果,让人误以为这棵树还未死去,年复一年地苟延残喘。
他只是静静地望着母亲癫狂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拱桥的尽头。柳祉没有追赶,震惊、悲伤、恐惧与迷茫像无形的绳索,紧紧束缚住了他的手脚。
他本该没有弟弟的,可偏偏在桥旁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啼哭。或许是出于对生命的怜悯,他蹲下身,凝视着这个被遗弃的婴儿。婴儿的皮肤透红,还有些皱巴巴的,柳祉从未见过自己那被丢进江里的弟弟的模样,但此刻,他想着,弟弟大概也是这样的吧。
柳祉没有停留太久。他站起身,冷风风打过他额前凌乱的发丝,吹得他眼中的泪水在稚嫩的脸庞上打了个转,最终悄然坠入江水之中。
远处的寥寥灯火明暗变换,普陵江中的神仙今夜格外贪婪。
家中的木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像是无休止的呻吟。床上的婴儿已经安然入睡。
柳祉有着菩萨般的心肠,救下了这个本该在寒风中或江水中消逝的生命;但他又仿佛是个十足的恶人,自私地将另一个生命拉入了这无尽的深渊。
当夜,那个双眼布满血丝、精神亢奋的男人回来了。他醉醺醺地沉浸在红红的票子中,得知自己的女人扔下孩子跑了后,只是嚷嚷着等赢了大钱要给柳祉找个“胸大腰细屁股圆”的小妈,嘴里还嘟囔着一些**什么的话。还抽出五十块钱,打发柳祉去买些好菜。
柳祉住在普陵江下游的小镇上。他借着月色,在走几步就到头、坑坑洼洼的砖路上,买了一些现成的猪杂碎——这类菜看起来分量不少,却花不了多少钱。剩下的钱,他悄悄塞进裤腰里,用布条腰带紧紧勒住,只将几块钱交给了那个男人。男人似乎真的在牌桌上赢了不少,没再细算,随手将钱塞进了口袋。
那一夜过后,断陵桥旁的弃婴成了他正式的弟弟。柳祉在用来糊柜子的乱七八糟的报纸和杂志上踮着脚找了半天,最终选了一个单字——“钰”。这个字既有“金”,又有“玉”,将来的小孩一定能温润如玉,富贵安康。
所以他的弟弟名叫柳钰。
他用偷偷留下的钱买了几包散装的奶粉,和在米汤里喂给柳钰。
那个年头,这边的城市经济萧条,更别提这了小村镇,一家里能出个工人每月赚个几百块日子过的都算滋润。自从有人走歪路子赚了钱,这一片的风气就如同集市上的臭鱼,腥臭糜烂。
宁安镇如今邻里之间都不走动,人情淡漠,有几家做起了违法买卖,这个当上了地头蛇,那个打家劫舍进了局子,柳祉家老爹不争气又不老实,正经过日子的人家不敢接济,道上的又没人看的起,人人自危的时候,日子过得一直很紧巴。
在柳祉出生前些年,困难到易子而食的家庭也是有的,小时候母亲最常念叨的就是说柳祉生在了好时候,可不知什么时候这句话就再也没从她嘴里说出来过。
柳钰的奶粉就算再怎么省着喝,也撑不了几天了。米汤根本不顶饿,孩子饿得哭得脸发紫,没什么肉感小手因长时间的哭泣而僵硬发麻。
将败的落日透过木框的玻璃窗,斜斜地洒在两个孩子的身上。一个费力地摇着啦另一个,哭声渐渐减弱后,他才半跪在床边,轻轻搓开婴儿那因哭泣而僵硬的小手,低声呢喃:
“哥哥不会再让你挨饿。”
一个孩童的眼中竟透出令人生畏的坚定。那未经世事的心里,刻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责任——照顾好弟弟。他恨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恨自己太小,无法为弟弟撑起一把伞。
第二天,他勉强让弟弟的肚子填饱后,便抱着孩子去了镇边的“献”血车。一只手紧紧搂着弟弟,另一只手的血液缓缓流出。他抽了三次血,才勉强凑够200毫升。
三个针孔,200毫升血,换来82块钱,足够柳钰喝上半个月的奶粉。在柳祉看来,这是一笔值得的交易。
他那小小的脑袋里只知道,血很值钱,能救弟弟的命。然而,那又粗又长的抽血针,却在柳祉的心脏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红痕,成为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伤痛。
出了献血车几步柳祉就倒在了镇边的桥洞上,不知多久,幼儿的哭声将他叫醒,他睁眼就是黑洞洞的一片,侧头剪见一个约莫四五十岁的男人怀里抱着柳钰,生疏的摇着孩子。
柳钰用手撑地强爬起来,警戒的盯着男人,如一只蓄势待发的小兽,男人也察觉到柳祉的敌意,努了努嘴,把哇哇哭的娃娃递给了柳祉。
“孩子好像饿了。”
“刚弄到钱,还没买奶粉呢。”
空气静了一瞬间,只剩下娃娃的哭声,男人向桥洞的一边望了望,又扫柳祉一眼,他在这待这么久,心下已经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