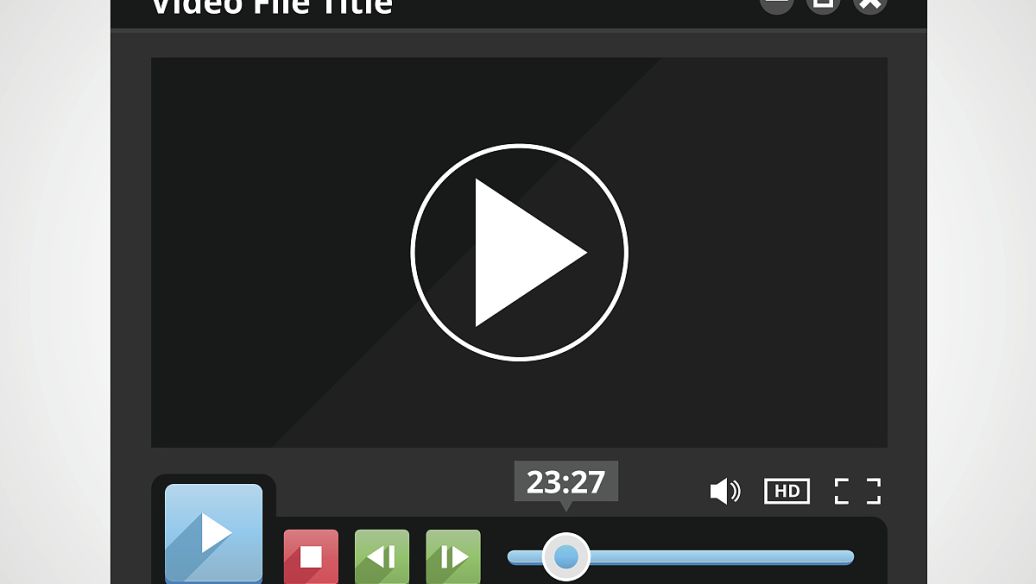煞白色的封条贴在门口,还崭新,讲的是:法院查封、严禁破坏。如你所见,我前半生的富贵逍遥,在二十九岁这年冬,被两张纸一叉一叠就变成了梦幻泡影,维港的风格外大,把围巾掀起来,穗子糊住了我的眼睛,我也的确不大想看,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叫形而上学么?不晓得,我念大学时,都扔两张票子找学生去读书,现在再想找人办事,已经没这么便宜的价格。
但除我之外,还有人也要面对这些,我姐姐的小孩、管我喊小舅舅的亲外甥,还在念国高,我在穗子摇摆的空隙中看见他,留的已经不是我离港前的妹妹头,长长成微分碎盖,跟随他那便宜爹的欧洲人骨相搭一块,漂亮得有棱有角。我看见他,沉默的、把嘴巴抿起来,好像我香烟盒紧闭着的盖子。
我想说,你真可怜,我好歹快活到了要奔三,你今年才一十七。
煞白色的封条贴在门口,还崭新,讲的是:法院查封、严禁破坏。如你所见,我前半生的富贵逍遥,在二十九岁这年冬,被两张纸一叉一叠就变成了梦幻泡影,维港的风格外大,把围巾掀起来,穗子糊住了我的眼睛,我也的确不大想看,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叫形而上学么?不晓得,我念大学时,都扔两张票子找学生去读书,现在再想找人办事,已经没这么便宜的价格。
但除我之外,还有人也要面对这些,我姐姐的小孩、管我喊小舅舅的亲外甥,还在念国高,我在穗子摇摆的空隙中看见他,留的已经不是我离港前的妹妹头,长长成微分碎盖,跟随他那便宜爹的欧洲人骨相搭一块,漂亮得有棱有角。我看见他,沉默的、把嘴巴抿起来,好像我香烟盒紧闭着的盖子。
我想说,你真可怜,我好歹快活到了要奔三,你今年才一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