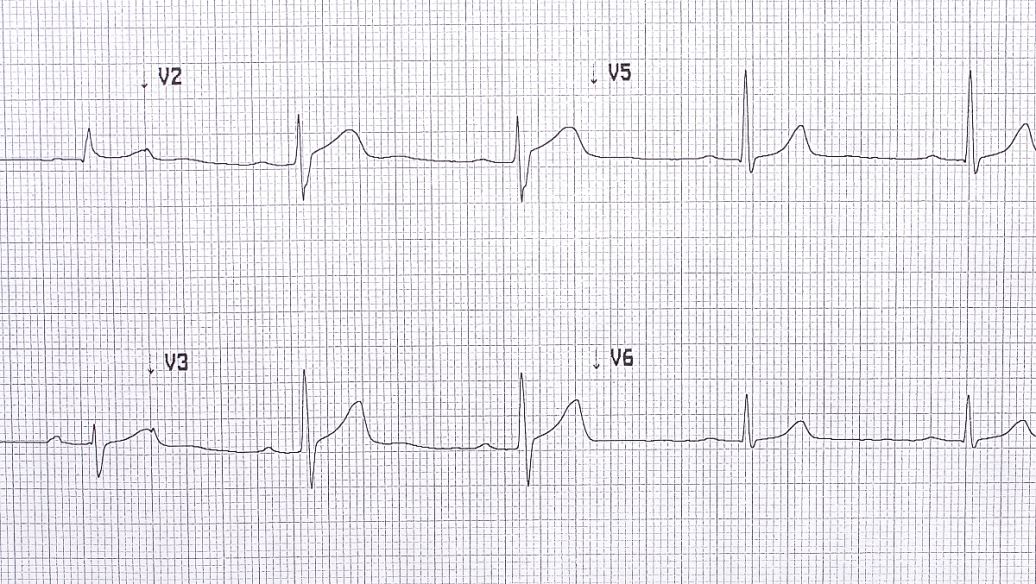首先是古体记梦诗。以篇幅较长的古体诗对梦境进行较为详细的叙写,这是以往记梦诗最常见的一种形态。如元稹五言古诗《感梦》共142句、《江陵三梦·其一》共72句,稍短一点的也不下二三十句,如白居易《梦与李七、庾三十三同访元九》为24句,韩愈《记梦》为28句等。入宋后也大抵如此,如梅尧臣《梦登河汉》44句、宋庠《壬子岁四月甲申夜纪梦》26句等。这一现象很容易理解:如无此等篇幅,不易完成对梦境的详细叙述。然而,陆游古体记梦诗的篇幅并不太长,多为16句、12句,基本在20句以内(含20句),仅有个别作品超过20句[17]。篇幅虽不长,对梦境的呈现却极为详细具体。如《记戊午十一月二十四夜梦》:
街南酒楼粲丹碧,万顷湖光照山色。我来半醉蹑危梯,坐客惊顾闻飞屐。长绦短帽黄絁裘,从一山童持药笈。近传老仙尝过市,此翁或是那可识?逡巡相语或稽首,争献名樽冀馀沥。我欲自言度不听,亦复轩然为专席。高谈方纵惊四座,不觉邻鸡呼梦破。人生自欺多类此,抚枕长谣识吾过。
街南酒楼粲丹碧,万顷湖光照山色。我来半醉蹑危梯,坐客惊顾闻飞屐。长绦短帽黄絁裘,从一山童持药笈。近传老仙尝过市,此翁或是那可识?逡巡相语或稽首,争献名樽冀馀沥。我欲自言度不听,亦复轩然为专席。高谈方纵惊四座,不觉邻鸡呼梦破。人生自欺多类此,抚枕长谣识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