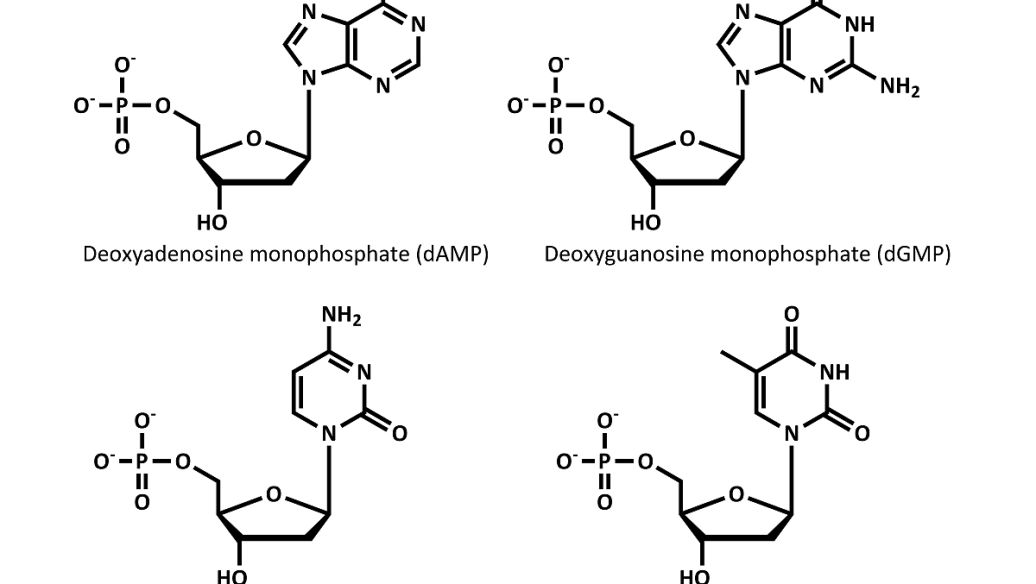卢明的水浒访谈录
问:卢明先生,我们想搞一个水浒访谈专题,请专家学者就水浒有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你是郓城人,水浒英雄宋江的同乡,对水浒做过不少研究,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卢明答: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本地人常说,郓城是水浒英雄的故乡。作为郓城人,很为英雄的故事而感到自豪。正因如此,我对水浒传有着较高的关注。当然,地域的因素只决定关注的重点,而不会干扰学术的公正性。无论谁,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应当以严谨的学风来研究水浒,不因文学以外的因素扭曲自己的观点。
问:我们要打造大水浒文化圈,整合水浒研究资源,这个文化圈,郓城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卢明:是的,郓城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点。水浒故事,关键事件与郓城有联系,关键人物也与郓城有联系。你提到水浒文化圈,我很感兴趣。我把水浒故事涉及的地域,划分成三个圈,这三个圈共以梁山泊为中心点。中心圈以百里为半径划圆,包括郓城、梁山、东平、阳谷等县,是水浒故事涉及最多的区域,当地人对水浒故事的关注度也最高。中间圈以五百里为半径划圆,包括大名、开封、高唐、青州、沂水、清河、东昌等地。这一地域,水浒故事有一些,但较之百里圈为少,关注水浒故事的人也没有中心圈多。外圈以千里为半径划圆,包括登州、蓟州、五台山、延安、渭州、江州、杭州等地。这一圆形带上,除杭州、江州外,多数地方涉及的水浒故事,只与特定的水浒人物和事件有关,当地人对水浒英雄与自己关系的认同度较弱。或许,在杭州、九江这些地方的旅游景点关于水浒的内容不算少,但,之一内容,在当地文化序列的排序,并不太靠前。这三个圈,包括宋朝统治的中心区和发达区,可以说是整个宋朝的北半部,也是施耐庵视野熟悉的区域。当然,所谓以多少里划圆,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并非地图上精确的度量。
我们研究水浒,应当兼顾这三个圈的全部。当然,作为山东人,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五百里圈,特别关注百里中心圈。
问:人常说:“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真有七十二人在郓城吗?
卢明答:这种说法,许多人都知道。至于说法源于何时,出自何人,恐怕难以考证。我觉得,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条:第一条,反映了郓城在水浒故事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第二条,反映了郓城人对水浒英雄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三条,说明郓城境内是水浒英雄的集中驻扎地。有人考查究竟哪些好汉在郓城,只查出晁盖.宋江.吴用.白胜.朱仝.雷横.宋清等人。但既有“七十二名在郓城“一说,自当有它的原因。其实,在北宋,梁山泊处于数县交界处,郓城领有其大半。梁山头领应当经常在郓城境内活动,进入过郓城境内的头领有七十二名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大家注意一个动词:是“在”郓城,而不是“生郓城”。
问:近年来,关于水浒,有不少新的观点,使人感觉耳目一新,你对此有何评论?
卢明答:学术崇尚创新,有新的观点,可以使人思路开阔。新的观点,也是思想多元化的产物。如果不是思想多元化,很多时候是一种观点压制了其他的不同观点。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角度,各种观点都有其产生的现实依据。我看到,近来有人否定水浒人物的英雄本色,把水浒人物看成是黑恶势力,是罪犯。这是换个角度看水浒。当然,并不是一定要标新立异才正确。有些观点,脱离《水浒传》固有的思想倾向和文本实际,那就扯远了。施耐庵有他的创作意图,水浒传有他的主题,这是客观体现在《水浒传》这部经典小说中的。
问:你认为,现代人应当怎样看待水浒?
卢明:水浒虽是一部小说,但它深刻反映了北宋末年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讴歌了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义军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对后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水浒描写的是北宋乱世,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太平盛世,所以,不能做比。关于怎样看水浒,有许多方面,我这里只讲以下三点:
第一,水浒传叙写的英雄故事和英雄气概,给人以冲天的豪气和战恶斗邪的勇气,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这样的阳刚之气,可以借来主持正义,惩恶扬善,冲锋杀敌。当然,见义勇为的时候,也要依法办事。赞赏鲁智深救金翠莲的义举,不学他打死镇关西的过失。
第二,水浒英雄被逼上梁山的命题反衬出反腐败的重要。毛主席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看透了水浒反抗的是政权组织中的贪腐集团,这贪腐既包括政治上的恶和经济上的贪及作风上的霸。英雄起义是高俅之流造成的。如果没有产生高俅那类恶官的土壤,政治清明,也就没有英雄起义的必要了。腐败,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要把反腐败斗争搞好,一切依序而行,社会才能安定祥和。
第三,水浒所反映的的时代有法不依造成社会动乱。反衬出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大家知道,宋代的法律是很完备的。但,再完备的法律,如果不严格执行,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如果人人都想钻法律的空子,并且能钻成,这社会也就不成体系了。水浒传故事里有法不依的事太多了。潘金莲勾奸夫害本夫,县衙却照顾西门庆的关系不依法办理,这才激起武松自行复仇的怒火。林冲剌配沧州,陆虞侯之流就能安排人私下结果他的性命。有法不依的时候,百姓对法律的依赖就失去了,政权的感信就荡然无存,所以说,司法腐败是最黑暗的腐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什么时候都需要坚持。
问:听说你把水浒英雄和西游记中的唐僧的三个徒弟做了类比,是什么样的类比?
卢明答:是的,乍看起来,二者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的经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相同之处,并且非常相同。
其一,他们起初都是社会低层的不安份者、既定秩序的反抗者、被主流社会丑恶化的异类。但,他们要求被平等对待的愿望强烈、打碎既定秩序的动力强大,与主流社会的斗争异常激烈。象孙悟空,出身没来历,官场不熟悉,上面没关系,却想象天宫的神仙一样,做个齐天大圣。被人家遇弄以后,就大闹天宫。宋江,身为押司,小吏一个,朝廷哪有他的位子?但,他带领梁山义军进行了激烈斗争,他的目标,也是象体制内的官员一样,有个为朝廷建功立业的位子。历次农民起义大概都是这种情形。被剥削压迫的底层人,走向反抗道路,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其二,他们都是逃不出统治者手心的失败者,招安后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一前一后,一身能耐使向两个完全向反的方面。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小白龙,都是被收编的妖魔,训化后一心想着完成统治者交付的使命来换取以后的功名。降妖除怪,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宋江等人受招安后征辽,打王庆,攻田虎,平方腊,都是为了立功给统治者看,也是为了扬名立万,最后大部分人也得了封号。
但,他们二者,也有一些不同。第一,悟空等人,是真的得了正果,每个人都成仙得到,结局是大圆满的。而宋江等人,在有了封号以后,多数人却受到奸臣的谄害含恨而死,结局是悲剧性的。尽管宋徽宗也在梁山上为他们立了靖忠之庙,但那已经是宋江等人饮恨屈死后了。不同的结局,体现的意义是不同的。悟空的结局,表明再冥玩不化的人只要受到统治者的调教,也能够成为统治集团立功出力的人。而宋江等人的结局,则表明了统治集团的凶险和恶毒。当然,有些人也可以归结为:投降没有好下场。我想,揭露北宋统治集团的凶险,才是施氏想表达的。第二,宋江等人面对的是现实的统治集团,而悟空等面对的是虚拟的神仙集团。当然,不管现实也好,神仙也好,反映的都是封建时代的政权体制。西游记体外再开一层,在天宫之上又设了个西天如来的体制。但,这个体制,仍然是现实体制和天宫体制的翻版。这也正说明,在那个时代,没有出现先进的阶级,历史的局限,使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体系。
这里还可以引入一个人物,就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其对既有秩序进行反抗上,贾宝玉和上面说的孙悟空、宋江等人,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孙、宋的反抗表现在政治方面,而贾的反抗更多体现在思想方面,反对封建思想,强调个性自由与解放。
问:为什么《水浒传》写裴如海和潘巧云的时候,要用一段文字来贬低讽刺和尚,这让少林弟子情何以堪?
卢明答:我想,这应当和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有关系。也就是说,作者对“偷情”持批判态度。他写潘、裴之间的情节,在于揭露荒淫。按照作者的思路看,连最应当戒欲的和尚都偷情,这真是可恶之极!
《水浒传》毕竟成书于封建时代,那时候宋明理学盛行,主流社会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男女偷情被看作最为可恨之事。另外,这种禁欲思想,还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在元末明初,社会混乱,因女人偷情而使老公家破人亡的屡有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这样的反感就很自然地出现在元杂剧和《水浒传》中了。
我们不能用现代生活和现代思维去强求古人。如果说古人有历史局限,那也是很难避免的,毕竟那是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封建时代,女子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独立性还不能实现。
我感觉,作者写潘氏偷情的故事,还是从一个角度写梁山好汉由正常生活走向草莽生涯的原因。
评心而论,要作和尚,就别偷情。重男女之情,就别当和尚。这涉及到信仰真不真的问题。
当然。偷情,在任何时代,都是不道德的。尽管有些不少情感是真实的,纯洁的。
问:穆弘的排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人曾质疑其参与了曾头市晁盖之死事件,您觉得晁盖之死是否有阴谋?穆弘有无参与这场阴谋?
卢明答:阴谋论早已有之,《水浒》评论大家金圣叹就是其中较早且较有影响的一个。后来不断有人参与进来。尤其是近年来,这个话题又被一些人翻出。
《水浒传》是小说,小说的情节主要是虚构的。研究小说与研究历史的根本不同,就是历史存在史书与史实的真与不真。小说则不用考虑这个,只看作者写了什么。作者写了,就是。作者没写,就不是。《水浒传》没有写晁盖之死在梁山集团内部有什么阴谋。所以,阴谋论在小说《水浒传》中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有些人那样想象,你不能不让他想。但那不是小说。我不认为晁盖之死有阴谋,所以,也就不存在穆弘参与不参与的问题了。
至于穆弘的排名,他在三十六天罡之中。这并不是《水浒传》的作者有什么偏私,而是由《水浒传》的流传生发史有关。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就有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的故事。《水浒传》的故事框架,主要来自于《大宋宣和遗事》,《遗事》中的三十六人名单,含穆弘(横),《水浒传》成书时,基本上是沿袭的这个名单,只有一两个作了调整。所以,穆横排三十六天罡之列,是情理中的事。如果把他调到后面,才是不正常的了。
问:请问水浒协会是个什么组织?
卢明答:不知道朋友在哪里听说的协会。
中国水浒学会是全国性的水浒研究学术组织,国家教育部主管,民政部备案的。
山东省、北京市、淅江省、湖北省等地都有省级水浒研究组织,有的叫水浒学会,有的叫水浒文化研究会。县级的水浒学术研究组织更多。这些学术组织,经常开展一些学动,主要是学术交流。
我就参加过一些这样的研讨会。我和中国水浒学会及上述省级水浒研究会的负责人都有联络。
问:原著里史文恭是不是被卢俊义突袭才被抓住的?卢俊义是单挑活捉史文恭吗?
卢明答:我记忆中,史文恭是在逃走的时候被卢俊义擒获的。卢俊义也不是没人配合。应当说,《水浒传》想突出表现的是卢俊义抓到了史文恭,只有这样故事才好写。
问:你对新版水浒电视剧里的武松怎么看?
卢明答:我对这新版水浒剧里的武松是认可的,认为体现了武松的精气神。
人们对水浒人物争论不少。对武松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但,差别不大。总体上认可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
当然,也有人说他在潘金莲面前不解风情,为施恩打蒋门神充当了打手。
可以肯定,《水浒传》作者绝对不会写武松对嫂子有情爱。如果那样写,不只违背了封建时代的伦理,而且有损于作者心目中武松的高大形象。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确是受人利用,但,作者想表现的是他的打抱不平,认为这才是英雄行为。站在武松的角度看问题,一个阶下囚,被管营高规格恩养,他一定是很感动。知恩不报非君子,这是绿林好汉的信条。
文学作品,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结合。所谓客观,就是要源于生活,符合艺术的真实。所谓主观,就是成熟的作品,一定反映了作者的主观评判。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结论。所以,才有〈水浒传〉对梁山好汉的张扬和《荡寇志》对梁山队伍的仇恨。这可以看出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问:现代很多人指责梁山好汉滥杀无辜,特别是对武松的质疑,不知道您如何看待武松“滥杀”?
卢明答:从人道主义出发,结合法制精神看,武松确有滥杀之嫌。比如,他把张督监全家都杀死了。
我们承认他滥杀,不赞成他滥杀。
全面地分析这个人物,把人物放回到他所处的环境中去考量,就可以看出,包括滥杀在内的所有情节设置,都是为了立体地塑造这个人物的需要。也就是说,武松这样的人,在那样的背景下,会做出那样的举动。这就显得真实。
另外,作者把张督监家作为整体的对立面看。比如打起仗来,很难仔细地区分敌对阵营中谁好谁不好,也就一味地仇视了。再说,张督监家的使女虽然受都监指使,但她无形中成了张都监等人的帮凶。当然,有的电视剧里写使女本贫家女,对武松有真感情,那是后人凭感觉改编的。原著里不是这样写的。
梁山将中,有滥杀毛病的人还有一些。比如李逵,比如解珍、解宝等。
滥杀是因为草莽。林冲夫人不滥杀,他只是个良家女子,成不了草莽英雄。
通过《水浒传》,我们知道,原来历史上的草莽人物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这就实现了小说的认识价值。滥杀不只水浒。真实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唐末黄巢的起义军还出现过人食人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应当说,《水浒传》这样写,不是写假了,而是体现了历史的真实。
问:不知道你最喜欢水浒传中哪一个人物?他有什么特别之处打动你?
卢明答:《水浒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人物画廊。许多水浒人物是相当可爱的。至于说最喜欢哪一个,这就很难用量化的办法筛选出来。象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杨志都是性格鲜明的,也都有其可爱之处。
如果非要说出个第一,我还是要说鲁智深。这个人力大,正义感特别强,是弱者保护神的形象。在他身上,突出地寄托着受期压者企盼保护的心理。他的出手相助,都是利他的,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无论是救金翠莲,救刘太公女儿,救林冲,这里面,既体现了仁,也体现了义。他正应了“风风火火闹九州”那句话。还有,在他身上,没有李逵、武松那样的“滥杀”,也没有王矮虎那样的调情,更没有时迁那样的偷盗。他是比较完美的,所以,《水浒传》一再强调他的佛性。
问:您在电视台做的水浒讲座还会继续吗?
卢明答:那个水浒讲坛,我做了十三讲,每讲半小时。去年初播近三个月,今年又重播了的两个月。喜欢看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视频,打关键字:水浒讲坛
除那十三讲外,我又写了十三讲内容。去年初冬,因于与山东电视台的孙玉平先生一起由山东到苏北考虑宋江起义的历史,误了录制。不过,所有二十六讲,我都整理成稿,并在山东省水浒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向与会朋友赠送。至于以后是不是录制,这要看具体情况。录制视频比单纯地写要复杂得多。
问:鲁智深确实很可爱,鄙人记得鲍鹏山教授在百家讲坛也是表现出很喜欢鲁大师,但是在点评武松时却用了另外一种批判产语气,于是在百度贴吧水浒圈子里有了两种对立群体,即鲁迷(拔树集团)和武迷(天人团)。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看过鲍鹏山教授对水浒传的讲座?对于他的观点您是否赞同呢?
卢明答:鲍鹏山先生是个很有名气的教授,学养深厚,我对他很敬重。他讲水浒的内容受众很多,我看过他的讲座,只是由于工作忙,断断续续地看过几讲,不系统。
对鲍先生的观点,我赞同的不少,不赞同的也有一些。不止我,我周围不少朋友都和我有同感,就是开始几讲听着很来劲,后来越听越感觉不对味。当然,这不是因为鲍先生讲得不好,而是我们很难接受他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
我感觉,鲍先生讲的好的地方,是生动具体地分析了鲁智深等人物的形象,与原著是一致的。我不赞同鲍先生的,是有些地方的分析,脱离了小说固有的规定性,并没有顾及《水浒传》这部古典名著统一的明确的思想脉络,这就出现了看起来有道理其实已经脱离了研究对象而自说自话的情况。对与水浒有关的话题,是可以见仁见智的,甚至可以用现代思维考查古人的得失,也就是跳出水浒看水浒。这是就一般社会问题而言,而不是分析小说。分析小说,一定要按照文学的规律,只有这样,才是文学评论。
分析小说,如果忽视了它的大的结构,就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小说的精神实质,就会出现偏差,就会出现一万种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失去了评价标准。比如,你只看孙二娘卖人肉包子,那就会说他是抢劫杀人犯。那就是片面的,因为没有顾及到她上梁山后替天行道故事。只有看全豹,才能得出:孙二娘虽然上山前干过不法的事,但上山后也成了为正义而战的好汉。瞎子摸象,说象腿是柱子。看起来对,其实不对。只有视力好的人能看到大象的全身,才不会说象的牙齿是宝剑。
问:总感觉宋江此人胸无大志,不敢把皇帝拉下马。
卢明答:历史上的宋江被记载很少,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完全没有方腊那样清晰。
小说塑造的宋江形象,必然受到故事流传及《水浒传》成书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况且,对它的塑造,有很多制约因素。比如:北宋本是被外族赶到南方去的,并非被农民起义推翻,你写他起义坚决,就没办法和历史大框架相吻合,这不是写刘邦。比如,在那个年代,作者不敢明目张胆地鼓吹起义,能写这些好汉已经是相当有胆量了。比如,他本另有意象,要的就是宋江的“不假称王”,肯定宋江忠君,这就容易通得过。所以才有明朝皇帝也读此书,才有地位相当高的郭勋等贵族刻印此书。
对于《水浒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解读。在革命年代,人们更多地注意到它的革命性。在和平年代,有人就更多地看到它的忠义。毛泽东起初更多地强调那些人物被“逼上梁山”,晚年却提出了《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是投降派的观点。
问:我觉着宋朝也是最奢靡的朝代。
卢明答:相对于开放的唐朝,宋朝就有很大变化了。这也是理学产生于宋的原因。不要因宋时有李师师之类的妓女,就认为一般的家庭生活伦理都开放。理学到了明代,就达到了完善期,对社会的实际影响也很大。而《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作者生活于这样的时代,封建思想自然是很重的。
问:石秀的排名为甚是33,老施喜欢阿秀这个人物给了他很多篇幅,为甚又让他死的那么容易,他的出现和之前的武二哥有甚联系,作者是在强调两郎还是二潘,石三郎真的是翻版武二郎吗?天慧星石秀确实是秀外慧中吗?
卢明答:这个问题,我想回答三点:
一、石秀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就在三十六位好汉之列,《水浒传》把他安排在三十六天罡之中,有其继承依据。只要了解这个发展过程,就不会对他的排名产生质疑。
二、在《水浒传》中,好多梁山好汉都在征方腊时死得容易,不独石秀。这也使不少读者感到不解。大概要把《水浒传》写成悲剧,也只能写他们一个个死得惨。还有一条,就是征辽是抵御外族统治,保卫大宋王朝,作者不想写英雄牺牲。打田虎王庆的故事是后加的,好多英雄好汉都能加了打方腊,如果写他们在打田虎王庆时就死去,就和后面的打方腊矛盾了。《水浒传》在细节的处理上,后半有草草了事的情况。这部名著后半部艺术性远远低于前七十回。
三、石秀的出场是在蓟州,他和杨雄的故事最多。他和武松在形象上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武艺高强,都喜欢打抱不平,都外表刚强而内心精细。但二人的故事有着不同的脉络,有些相似并不足以说谁是谁的翻版。《水浒传》不像有些小说那样力避重复,而是敢于相“犯”,善于在相似中写出不同(金圣叹先生就专门提到此事)。比如写淫妇,写了阎婆惜,还写潘金莲,又写潘巧云。写鲁智深救人,写了救金翠莲,又写救刘太公女儿,再写救林冲。这大概是有些人把二潘联系起来看的原因。写事件如此,写人物也有这类情况。比如写鲁智深的鲁莽,又写李逵的鲁莽。但细看,二人又有很大的不同。
说石秀秀外慧中,这很符合他的实际。
问:作者借晁盖之死来影射小明王之死。
卢明答:这是一种猜想。在《水浒传》成书前,无论是讲史话本还是元杂剧,都说晁盖在宋江上山时已经死去,《水浒传》写晁盖死去是继承的前人,而不是自己的创造。何况,水浒故事是以历史上宋江领导的农民军的事迹为描写对象。从小说营造的角度看,如果晁盖不死,就没办法突出宋江。
《水浒传》底本《大宋宣和遗事》产生于南宋或稍晚,小明王的事发生在元末,是先有晁盖早死的说法,而后才有小明王出世。至于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把民间长期流传的故事编成《水浒传》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小明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代人编辑故事,写施耐庵,编他这样那样,不能代表文学发展的实际。
元杂剧中,晁盖是栾廷玉射死的,不是史文恭。但也说明在杂剧中,晁盖就是被人射死的。了解了水浒故事的流传过程,现代的一些臆测就可以消除了。
问:卢明先生,我们想搞一个水浒访谈专题,请专家学者就水浒有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你是郓城人,水浒英雄宋江的同乡,对水浒做过不少研究,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卢明答: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本地人常说,郓城是水浒英雄的故乡。作为郓城人,很为英雄的故事而感到自豪。正因如此,我对水浒传有着较高的关注。当然,地域的因素只决定关注的重点,而不会干扰学术的公正性。无论谁,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应当以严谨的学风来研究水浒,不因文学以外的因素扭曲自己的观点。
问:我们要打造大水浒文化圈,整合水浒研究资源,这个文化圈,郓城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卢明:是的,郓城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点。水浒故事,关键事件与郓城有联系,关键人物也与郓城有联系。你提到水浒文化圈,我很感兴趣。我把水浒故事涉及的地域,划分成三个圈,这三个圈共以梁山泊为中心点。中心圈以百里为半径划圆,包括郓城、梁山、东平、阳谷等县,是水浒故事涉及最多的区域,当地人对水浒故事的关注度也最高。中间圈以五百里为半径划圆,包括大名、开封、高唐、青州、沂水、清河、东昌等地。这一地域,水浒故事有一些,但较之百里圈为少,关注水浒故事的人也没有中心圈多。外圈以千里为半径划圆,包括登州、蓟州、五台山、延安、渭州、江州、杭州等地。这一圆形带上,除杭州、江州外,多数地方涉及的水浒故事,只与特定的水浒人物和事件有关,当地人对水浒英雄与自己关系的认同度较弱。或许,在杭州、九江这些地方的旅游景点关于水浒的内容不算少,但,之一内容,在当地文化序列的排序,并不太靠前。这三个圈,包括宋朝统治的中心区和发达区,可以说是整个宋朝的北半部,也是施耐庵视野熟悉的区域。当然,所谓以多少里划圆,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并非地图上精确的度量。
我们研究水浒,应当兼顾这三个圈的全部。当然,作为山东人,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五百里圈,特别关注百里中心圈。
问:人常说:“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真有七十二人在郓城吗?
卢明答:这种说法,许多人都知道。至于说法源于何时,出自何人,恐怕难以考证。我觉得,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条:第一条,反映了郓城在水浒故事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第二条,反映了郓城人对水浒英雄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三条,说明郓城境内是水浒英雄的集中驻扎地。有人考查究竟哪些好汉在郓城,只查出晁盖.宋江.吴用.白胜.朱仝.雷横.宋清等人。但既有“七十二名在郓城“一说,自当有它的原因。其实,在北宋,梁山泊处于数县交界处,郓城领有其大半。梁山头领应当经常在郓城境内活动,进入过郓城境内的头领有七十二名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大家注意一个动词:是“在”郓城,而不是“生郓城”。
问:近年来,关于水浒,有不少新的观点,使人感觉耳目一新,你对此有何评论?
卢明答:学术崇尚创新,有新的观点,可以使人思路开阔。新的观点,也是思想多元化的产物。如果不是思想多元化,很多时候是一种观点压制了其他的不同观点。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角度,各种观点都有其产生的现实依据。我看到,近来有人否定水浒人物的英雄本色,把水浒人物看成是黑恶势力,是罪犯。这是换个角度看水浒。当然,并不是一定要标新立异才正确。有些观点,脱离《水浒传》固有的思想倾向和文本实际,那就扯远了。施耐庵有他的创作意图,水浒传有他的主题,这是客观体现在《水浒传》这部经典小说中的。
问:你认为,现代人应当怎样看待水浒?
卢明:水浒虽是一部小说,但它深刻反映了北宋末年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讴歌了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义军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对后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水浒描写的是北宋乱世,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太平盛世,所以,不能做比。关于怎样看水浒,有许多方面,我这里只讲以下三点:
第一,水浒传叙写的英雄故事和英雄气概,给人以冲天的豪气和战恶斗邪的勇气,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这样的阳刚之气,可以借来主持正义,惩恶扬善,冲锋杀敌。当然,见义勇为的时候,也要依法办事。赞赏鲁智深救金翠莲的义举,不学他打死镇关西的过失。
第二,水浒英雄被逼上梁山的命题反衬出反腐败的重要。毛主席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看透了水浒反抗的是政权组织中的贪腐集团,这贪腐既包括政治上的恶和经济上的贪及作风上的霸。英雄起义是高俅之流造成的。如果没有产生高俅那类恶官的土壤,政治清明,也就没有英雄起义的必要了。腐败,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要把反腐败斗争搞好,一切依序而行,社会才能安定祥和。
第三,水浒所反映的的时代有法不依造成社会动乱。反衬出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大家知道,宋代的法律是很完备的。但,再完备的法律,如果不严格执行,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如果人人都想钻法律的空子,并且能钻成,这社会也就不成体系了。水浒传故事里有法不依的事太多了。潘金莲勾奸夫害本夫,县衙却照顾西门庆的关系不依法办理,这才激起武松自行复仇的怒火。林冲剌配沧州,陆虞侯之流就能安排人私下结果他的性命。有法不依的时候,百姓对法律的依赖就失去了,政权的感信就荡然无存,所以说,司法腐败是最黑暗的腐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什么时候都需要坚持。
问:听说你把水浒英雄和西游记中的唐僧的三个徒弟做了类比,是什么样的类比?
卢明答:是的,乍看起来,二者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的经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相同之处,并且非常相同。
其一,他们起初都是社会低层的不安份者、既定秩序的反抗者、被主流社会丑恶化的异类。但,他们要求被平等对待的愿望强烈、打碎既定秩序的动力强大,与主流社会的斗争异常激烈。象孙悟空,出身没来历,官场不熟悉,上面没关系,却想象天宫的神仙一样,做个齐天大圣。被人家遇弄以后,就大闹天宫。宋江,身为押司,小吏一个,朝廷哪有他的位子?但,他带领梁山义军进行了激烈斗争,他的目标,也是象体制内的官员一样,有个为朝廷建功立业的位子。历次农民起义大概都是这种情形。被剥削压迫的底层人,走向反抗道路,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其二,他们都是逃不出统治者手心的失败者,招安后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一前一后,一身能耐使向两个完全向反的方面。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小白龙,都是被收编的妖魔,训化后一心想着完成统治者交付的使命来换取以后的功名。降妖除怪,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宋江等人受招安后征辽,打王庆,攻田虎,平方腊,都是为了立功给统治者看,也是为了扬名立万,最后大部分人也得了封号。
但,他们二者,也有一些不同。第一,悟空等人,是真的得了正果,每个人都成仙得到,结局是大圆满的。而宋江等人,在有了封号以后,多数人却受到奸臣的谄害含恨而死,结局是悲剧性的。尽管宋徽宗也在梁山上为他们立了靖忠之庙,但那已经是宋江等人饮恨屈死后了。不同的结局,体现的意义是不同的。悟空的结局,表明再冥玩不化的人只要受到统治者的调教,也能够成为统治集团立功出力的人。而宋江等人的结局,则表明了统治集团的凶险和恶毒。当然,有些人也可以归结为:投降没有好下场。我想,揭露北宋统治集团的凶险,才是施氏想表达的。第二,宋江等人面对的是现实的统治集团,而悟空等面对的是虚拟的神仙集团。当然,不管现实也好,神仙也好,反映的都是封建时代的政权体制。西游记体外再开一层,在天宫之上又设了个西天如来的体制。但,这个体制,仍然是现实体制和天宫体制的翻版。这也正说明,在那个时代,没有出现先进的阶级,历史的局限,使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体系。
这里还可以引入一个人物,就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其对既有秩序进行反抗上,贾宝玉和上面说的孙悟空、宋江等人,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孙、宋的反抗表现在政治方面,而贾的反抗更多体现在思想方面,反对封建思想,强调个性自由与解放。
问:为什么《水浒传》写裴如海和潘巧云的时候,要用一段文字来贬低讽刺和尚,这让少林弟子情何以堪?
卢明答:我想,这应当和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有关系。也就是说,作者对“偷情”持批判态度。他写潘、裴之间的情节,在于揭露荒淫。按照作者的思路看,连最应当戒欲的和尚都偷情,这真是可恶之极!
《水浒传》毕竟成书于封建时代,那时候宋明理学盛行,主流社会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男女偷情被看作最为可恨之事。另外,这种禁欲思想,还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在元末明初,社会混乱,因女人偷情而使老公家破人亡的屡有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这样的反感就很自然地出现在元杂剧和《水浒传》中了。
我们不能用现代生活和现代思维去强求古人。如果说古人有历史局限,那也是很难避免的,毕竟那是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封建时代,女子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独立性还不能实现。
我感觉,作者写潘氏偷情的故事,还是从一个角度写梁山好汉由正常生活走向草莽生涯的原因。
评心而论,要作和尚,就别偷情。重男女之情,就别当和尚。这涉及到信仰真不真的问题。
当然。偷情,在任何时代,都是不道德的。尽管有些不少情感是真实的,纯洁的。
问:穆弘的排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人曾质疑其参与了曾头市晁盖之死事件,您觉得晁盖之死是否有阴谋?穆弘有无参与这场阴谋?
卢明答:阴谋论早已有之,《水浒》评论大家金圣叹就是其中较早且较有影响的一个。后来不断有人参与进来。尤其是近年来,这个话题又被一些人翻出。
《水浒传》是小说,小说的情节主要是虚构的。研究小说与研究历史的根本不同,就是历史存在史书与史实的真与不真。小说则不用考虑这个,只看作者写了什么。作者写了,就是。作者没写,就不是。《水浒传》没有写晁盖之死在梁山集团内部有什么阴谋。所以,阴谋论在小说《水浒传》中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有些人那样想象,你不能不让他想。但那不是小说。我不认为晁盖之死有阴谋,所以,也就不存在穆弘参与不参与的问题了。
至于穆弘的排名,他在三十六天罡之中。这并不是《水浒传》的作者有什么偏私,而是由《水浒传》的流传生发史有关。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就有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的故事。《水浒传》的故事框架,主要来自于《大宋宣和遗事》,《遗事》中的三十六人名单,含穆弘(横),《水浒传》成书时,基本上是沿袭的这个名单,只有一两个作了调整。所以,穆横排三十六天罡之列,是情理中的事。如果把他调到后面,才是不正常的了。
问:请问水浒协会是个什么组织?
卢明答:不知道朋友在哪里听说的协会。
中国水浒学会是全国性的水浒研究学术组织,国家教育部主管,民政部备案的。
山东省、北京市、淅江省、湖北省等地都有省级水浒研究组织,有的叫水浒学会,有的叫水浒文化研究会。县级的水浒学术研究组织更多。这些学术组织,经常开展一些学动,主要是学术交流。
我就参加过一些这样的研讨会。我和中国水浒学会及上述省级水浒研究会的负责人都有联络。
问:原著里史文恭是不是被卢俊义突袭才被抓住的?卢俊义是单挑活捉史文恭吗?
卢明答:我记忆中,史文恭是在逃走的时候被卢俊义擒获的。卢俊义也不是没人配合。应当说,《水浒传》想突出表现的是卢俊义抓到了史文恭,只有这样故事才好写。
问:你对新版水浒电视剧里的武松怎么看?
卢明答:我对这新版水浒剧里的武松是认可的,认为体现了武松的精气神。
人们对水浒人物争论不少。对武松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但,差别不大。总体上认可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
当然,也有人说他在潘金莲面前不解风情,为施恩打蒋门神充当了打手。
可以肯定,《水浒传》作者绝对不会写武松对嫂子有情爱。如果那样写,不只违背了封建时代的伦理,而且有损于作者心目中武松的高大形象。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确是受人利用,但,作者想表现的是他的打抱不平,认为这才是英雄行为。站在武松的角度看问题,一个阶下囚,被管营高规格恩养,他一定是很感动。知恩不报非君子,这是绿林好汉的信条。
文学作品,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结合。所谓客观,就是要源于生活,符合艺术的真实。所谓主观,就是成熟的作品,一定反映了作者的主观评判。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结论。所以,才有〈水浒传〉对梁山好汉的张扬和《荡寇志》对梁山队伍的仇恨。这可以看出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问:现代很多人指责梁山好汉滥杀无辜,特别是对武松的质疑,不知道您如何看待武松“滥杀”?
卢明答:从人道主义出发,结合法制精神看,武松确有滥杀之嫌。比如,他把张督监全家都杀死了。
我们承认他滥杀,不赞成他滥杀。
全面地分析这个人物,把人物放回到他所处的环境中去考量,就可以看出,包括滥杀在内的所有情节设置,都是为了立体地塑造这个人物的需要。也就是说,武松这样的人,在那样的背景下,会做出那样的举动。这就显得真实。
另外,作者把张督监家作为整体的对立面看。比如打起仗来,很难仔细地区分敌对阵营中谁好谁不好,也就一味地仇视了。再说,张督监家的使女虽然受都监指使,但她无形中成了张都监等人的帮凶。当然,有的电视剧里写使女本贫家女,对武松有真感情,那是后人凭感觉改编的。原著里不是这样写的。
梁山将中,有滥杀毛病的人还有一些。比如李逵,比如解珍、解宝等。
滥杀是因为草莽。林冲夫人不滥杀,他只是个良家女子,成不了草莽英雄。
通过《水浒传》,我们知道,原来历史上的草莽人物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这就实现了小说的认识价值。滥杀不只水浒。真实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唐末黄巢的起义军还出现过人食人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应当说,《水浒传》这样写,不是写假了,而是体现了历史的真实。
问:不知道你最喜欢水浒传中哪一个人物?他有什么特别之处打动你?
卢明答:《水浒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人物画廊。许多水浒人物是相当可爱的。至于说最喜欢哪一个,这就很难用量化的办法筛选出来。象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杨志都是性格鲜明的,也都有其可爱之处。
如果非要说出个第一,我还是要说鲁智深。这个人力大,正义感特别强,是弱者保护神的形象。在他身上,突出地寄托着受期压者企盼保护的心理。他的出手相助,都是利他的,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无论是救金翠莲,救刘太公女儿,救林冲,这里面,既体现了仁,也体现了义。他正应了“风风火火闹九州”那句话。还有,在他身上,没有李逵、武松那样的“滥杀”,也没有王矮虎那样的调情,更没有时迁那样的偷盗。他是比较完美的,所以,《水浒传》一再强调他的佛性。
问:您在电视台做的水浒讲座还会继续吗?
卢明答:那个水浒讲坛,我做了十三讲,每讲半小时。去年初播近三个月,今年又重播了的两个月。喜欢看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视频,打关键字:水浒讲坛
除那十三讲外,我又写了十三讲内容。去年初冬,因于与山东电视台的孙玉平先生一起由山东到苏北考虑宋江起义的历史,误了录制。不过,所有二十六讲,我都整理成稿,并在山东省水浒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向与会朋友赠送。至于以后是不是录制,这要看具体情况。录制视频比单纯地写要复杂得多。
问:鲁智深确实很可爱,鄙人记得鲍鹏山教授在百家讲坛也是表现出很喜欢鲁大师,但是在点评武松时却用了另外一种批判产语气,于是在百度贴吧水浒圈子里有了两种对立群体,即鲁迷(拔树集团)和武迷(天人团)。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看过鲍鹏山教授对水浒传的讲座?对于他的观点您是否赞同呢?
卢明答:鲍鹏山先生是个很有名气的教授,学养深厚,我对他很敬重。他讲水浒的内容受众很多,我看过他的讲座,只是由于工作忙,断断续续地看过几讲,不系统。
对鲍先生的观点,我赞同的不少,不赞同的也有一些。不止我,我周围不少朋友都和我有同感,就是开始几讲听着很来劲,后来越听越感觉不对味。当然,这不是因为鲍先生讲得不好,而是我们很难接受他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
我感觉,鲍先生讲的好的地方,是生动具体地分析了鲁智深等人物的形象,与原著是一致的。我不赞同鲍先生的,是有些地方的分析,脱离了小说固有的规定性,并没有顾及《水浒传》这部古典名著统一的明确的思想脉络,这就出现了看起来有道理其实已经脱离了研究对象而自说自话的情况。对与水浒有关的话题,是可以见仁见智的,甚至可以用现代思维考查古人的得失,也就是跳出水浒看水浒。这是就一般社会问题而言,而不是分析小说。分析小说,一定要按照文学的规律,只有这样,才是文学评论。
分析小说,如果忽视了它的大的结构,就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小说的精神实质,就会出现偏差,就会出现一万种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失去了评价标准。比如,你只看孙二娘卖人肉包子,那就会说他是抢劫杀人犯。那就是片面的,因为没有顾及到她上梁山后替天行道故事。只有看全豹,才能得出:孙二娘虽然上山前干过不法的事,但上山后也成了为正义而战的好汉。瞎子摸象,说象腿是柱子。看起来对,其实不对。只有视力好的人能看到大象的全身,才不会说象的牙齿是宝剑。
问:总感觉宋江此人胸无大志,不敢把皇帝拉下马。
卢明答:历史上的宋江被记载很少,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完全没有方腊那样清晰。
小说塑造的宋江形象,必然受到故事流传及《水浒传》成书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况且,对它的塑造,有很多制约因素。比如:北宋本是被外族赶到南方去的,并非被农民起义推翻,你写他起义坚决,就没办法和历史大框架相吻合,这不是写刘邦。比如,在那个年代,作者不敢明目张胆地鼓吹起义,能写这些好汉已经是相当有胆量了。比如,他本另有意象,要的就是宋江的“不假称王”,肯定宋江忠君,这就容易通得过。所以才有明朝皇帝也读此书,才有地位相当高的郭勋等贵族刻印此书。
对于《水浒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解读。在革命年代,人们更多地注意到它的革命性。在和平年代,有人就更多地看到它的忠义。毛泽东起初更多地强调那些人物被“逼上梁山”,晚年却提出了《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是投降派的观点。
问:我觉着宋朝也是最奢靡的朝代。
卢明答:相对于开放的唐朝,宋朝就有很大变化了。这也是理学产生于宋的原因。不要因宋时有李师师之类的妓女,就认为一般的家庭生活伦理都开放。理学到了明代,就达到了完善期,对社会的实际影响也很大。而《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作者生活于这样的时代,封建思想自然是很重的。
问:石秀的排名为甚是33,老施喜欢阿秀这个人物给了他很多篇幅,为甚又让他死的那么容易,他的出现和之前的武二哥有甚联系,作者是在强调两郎还是二潘,石三郎真的是翻版武二郎吗?天慧星石秀确实是秀外慧中吗?
卢明答:这个问题,我想回答三点:
一、石秀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就在三十六位好汉之列,《水浒传》把他安排在三十六天罡之中,有其继承依据。只要了解这个发展过程,就不会对他的排名产生质疑。
二、在《水浒传》中,好多梁山好汉都在征方腊时死得容易,不独石秀。这也使不少读者感到不解。大概要把《水浒传》写成悲剧,也只能写他们一个个死得惨。还有一条,就是征辽是抵御外族统治,保卫大宋王朝,作者不想写英雄牺牲。打田虎王庆的故事是后加的,好多英雄好汉都能加了打方腊,如果写他们在打田虎王庆时就死去,就和后面的打方腊矛盾了。《水浒传》在细节的处理上,后半有草草了事的情况。这部名著后半部艺术性远远低于前七十回。
三、石秀的出场是在蓟州,他和杨雄的故事最多。他和武松在形象上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武艺高强,都喜欢打抱不平,都外表刚强而内心精细。但二人的故事有着不同的脉络,有些相似并不足以说谁是谁的翻版。《水浒传》不像有些小说那样力避重复,而是敢于相“犯”,善于在相似中写出不同(金圣叹先生就专门提到此事)。比如写淫妇,写了阎婆惜,还写潘金莲,又写潘巧云。写鲁智深救人,写了救金翠莲,又写救刘太公女儿,再写救林冲。这大概是有些人把二潘联系起来看的原因。写事件如此,写人物也有这类情况。比如写鲁智深的鲁莽,又写李逵的鲁莽。但细看,二人又有很大的不同。
说石秀秀外慧中,这很符合他的实际。
问:作者借晁盖之死来影射小明王之死。
卢明答:这是一种猜想。在《水浒传》成书前,无论是讲史话本还是元杂剧,都说晁盖在宋江上山时已经死去,《水浒传》写晁盖死去是继承的前人,而不是自己的创造。何况,水浒故事是以历史上宋江领导的农民军的事迹为描写对象。从小说营造的角度看,如果晁盖不死,就没办法突出宋江。
《水浒传》底本《大宋宣和遗事》产生于南宋或稍晚,小明王的事发生在元末,是先有晁盖早死的说法,而后才有小明王出世。至于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把民间长期流传的故事编成《水浒传》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小明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代人编辑故事,写施耐庵,编他这样那样,不能代表文学发展的实际。
元杂剧中,晁盖是栾廷玉射死的,不是史文恭。但也说明在杂剧中,晁盖就是被人射死的。了解了水浒故事的流传过程,现代的一些臆测就可以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