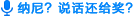余绔
它似乎是高耸如云的,却又像是只因金光灼眼而使人难望其项背;它似乎是冰冷拒人的,却又仿佛是过近的挑逗而隔了层难言的疏离。门口的侍者衣着统一的制度,每个赌场周围都少不了一些带着五大三粗的金链子晃悠的放高利贷的人,他们就像狼,而你就是他们的猎物盯着你阴狠的眼睛里泛着毫不掩饰的贪婪的绿光。
抖了抖身上合体剪裁的黑色西装扣上胸前的纽扣抬步向门口走去。经过门口的安检,听着三三两两的人上楼皮鞋于光亮的大理石地面摩擦发出“嗒嗒”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似是带着一丝沉重,不知自己即将到达的地方是天堂还是地狱。整个大厅以金色为主任何词语都无法形容出它的奢靡。场内的钟声、电子音乐及硬币撞击金属盘的声音,交织出只有在赌场能听到的典型乐章。
踩着脚下名贵的绣着繁复纹样的地毯穿梭在熙攘的人群中,找了在世界各地赌场中最受欢迎的赌戏之一——百家乐的赌桌。劳烦侍者去给我兑换了些筹码,抬手解开里面衬衫领口处的扣子,这才嘴角带着微笑迎视上原来就落坐在这儿的几位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打量的目光,不紧不慢的开口
:“我特地来见识此地赌场的风土人情,在大厅中看了一圈见这桌玩的挺好,不知我个外地人能否有幸与几位玩上几盘?”
那几位虽神态各异但也谁都没说什么,侍者此刻也将兑换好的筹码放在面前的桌上,对面的几位以及周围围观的人群带着讥笑的语言传进我的耳朵里,我这仅仅的十块在他们堆积如山的筹码面前的确显得有些可怜。恍若未闻的将面前全部的筹码推到赌桌中间,颔首示意其它几位也下注,好整以暇的看着专业的荷官将纸牌从牌盒中分发,一盘盘下来面前的筹码越堆越多,周围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由原来的讥笑转变为不可思议现在已经是安静到了开牌的时候才会有几处嘶声。
它似乎是高耸如云的,却又像是只因金光灼眼而使人难望其项背;它似乎是冰冷拒人的,却又仿佛是过近的挑逗而隔了层难言的疏离。门口的侍者衣着统一的制度,每个赌场周围都少不了一些带着五大三粗的金链子晃悠的放高利贷的人,他们就像狼,而你就是他们的猎物盯着你阴狠的眼睛里泛着毫不掩饰的贪婪的绿光。
抖了抖身上合体剪裁的黑色西装扣上胸前的纽扣抬步向门口走去。经过门口的安检,听着三三两两的人上楼皮鞋于光亮的大理石地面摩擦发出“嗒嗒”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似是带着一丝沉重,不知自己即将到达的地方是天堂还是地狱。整个大厅以金色为主任何词语都无法形容出它的奢靡。场内的钟声、电子音乐及硬币撞击金属盘的声音,交织出只有在赌场能听到的典型乐章。
踩着脚下名贵的绣着繁复纹样的地毯穿梭在熙攘的人群中,找了在世界各地赌场中最受欢迎的赌戏之一——百家乐的赌桌。劳烦侍者去给我兑换了些筹码,抬手解开里面衬衫领口处的扣子,这才嘴角带着微笑迎视上原来就落坐在这儿的几位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打量的目光,不紧不慢的开口
:“我特地来见识此地赌场的风土人情,在大厅中看了一圈见这桌玩的挺好,不知我个外地人能否有幸与几位玩上几盘?”
那几位虽神态各异但也谁都没说什么,侍者此刻也将兑换好的筹码放在面前的桌上,对面的几位以及周围围观的人群带着讥笑的语言传进我的耳朵里,我这仅仅的十块在他们堆积如山的筹码面前的确显得有些可怜。恍若未闻的将面前全部的筹码推到赌桌中间,颔首示意其它几位也下注,好整以暇的看着专业的荷官将纸牌从牌盒中分发,一盘盘下来面前的筹码越堆越多,周围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由原来的讥笑转变为不可思议现在已经是安静到了开牌的时候才会有几处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