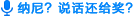“走,师兄带你看蔷薇去。”
那年清明,夜里,陵越私自带着屠苏下了山,走的很急,将春水杜鹃染过的红绫松松往屠苏发上一系,就当是梳过了头。
阁门空响,屠苏回过头去,小灯摇曳,桌案上半摊开一卷书札,墨迹未干,那是清晨陵越才抄录完的经书,他念一句,屠苏就跟着念一句,圣贤断绝五色声香味触法,坐看须弥日月,六道无常。
清明时节,人间已是春气芳菲,天墉城位于昆仑山绝顶,七十二峰,积雪终年不化,坐在屋檐下时,便能听到流转其间的呜呜风声,清冷寒意缭绕眉睫。这样的天气,无怪屠苏偷偷养的一盆蔷薇冻伤了。如今本该是花期,乌瓷花盆里的花枝花叶可怜兮兮的蜷缩起来,屠苏看见了也没有说什么,只默默的把盆中枯萎凋败的春色连根拔起,丢进了后院的小潭。陵越这才想起,屈指算来,屠苏从他来时,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天墉城了。
没来由的,他想带屠苏去看一回清明雨里的蔷薇花。就算是圆满了他一场花开的愿景。
“师兄就不怕掌教和师尊责怪。”
屠苏不自觉握紧了陵越的手,脚步轻快了起来。
“若我被责罚了,屠苏也要罚。”陵越微扬起了唇角,“罚你去剑阁,端茶倒水。”
陵越说罢,屠苏许久没有回答他,陵越只以为他当了真,正要回过头去和屠苏解释,却望见屠苏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开了口,“我替师兄多带几束蔷薇回去,掌和师尊见了喜欢,就不罚了。”
“你怎知掌教和师尊喜欢花儿?”陵越失笑。
屠苏抿了抿唇,乌黑睫羽扑簌一闪,“我猜的。”
去时还有月亮,一步一步往山下去,暖意也随着一步一步萦绕上来,渐见了街市烟火,一条清清小河,弯弯曲曲往远方流去,月亮的倒影上落着几穗青青的柳花。两岸张着仕女的游春锦帐,浅碧绛红,水面泊着莲灯,光芒星星点点忽远忽近,却不知去何处才能看见蔷薇,陵越住了脚步,对屠苏道。
“我去问路。”
屠苏望着师兄,点了点头,立在河岸边。
陵越的身影渐渐去远了,屠苏收回目光,一盏灯被对岸人送到面前,风一吹,又转了一个弯,重重叠叠的花心里放着一张手掌大小的红笺,红笺上依稀有字迹,屠苏想看看纸上写的究竟是什么,而花灯越飘越远,终究是看不见了,他只得再立回河岸边,这片刻,他不知是更想师兄了,还是更不想了。陵越一会就回来了,想是问清了看花的路,他手里却多了一只红烛,红烛上系着一根点缀金粟长长的鸳鸯绣带。屠苏望他,陵越弓起手指,抵在鼻翼下轻咳了一声,“那边鹅黄罗帐后的姑娘跟我讲,能看花的地方,不曾有灯。”片刻他又补了一句。
“红烛是猜谜得的。”
屠苏伸手将垂落到地上的绣带挽起来,风将鸳鸯,缠绕在指尖。他抬起头来看他。
“什么谜。”
远处鹅黄罗帐外,有藕丝柳裙飘扬,往陵越屠苏二人这边看,素绢小罗扇一摇一摆。
“戍边走千里,草下有鱼禾。”
“师兄没有猜出来。”陵越向他道,“姑娘便嫌师兄笨,可怜师兄,就送了支红烛。”
屠苏听的愣了,心念一动,望向陵越。
陵越没有看他,将红烛收在袖里,“走吧。”
隔岸铃鼓踏摇,绣带上的鸳鸯又坠落在衣角。
只是陵越手里的红烛还是没能点亮来看花,他们来的太晚,小园已上了锁,门前寂静无人。陵越陪着屠苏在门前站了一会,才说,走吧。
清明节的蔷薇终究是没能看见,来时的河岸人也走尽,落花和烟火散落了一地,屠苏随着陵越走过生满青青郁草的岸上,突然记起来陵越去取红烛时,他自己一个人站在河堤,在水里看见的那盏莲灯,莲灯的花心放了一张红笺,如今,灯已经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但是屠苏仍旧想知道,那张红笺上写的字。
“戍边走千里,草下有鱼禾。”
他又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将目光落在烟月摇曳的河上,只当是那张红笺上,写的就是这十个字。
说的是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个人去遥远的边关驻守,边关离他的家有一千里,他走的时候,还记得小小妻子站在水田边,青青禾草间还有小小的红色鱼儿在游荡。
有过了很久很久,他走了一千里又回到了家,青青的禾草间,红色的鱼儿还在游来游去。
那个人记得小小的妻子和红鱼儿,小小的妻子和红鱼儿也记得他,都一起在等他回来。
我也记得你,把这十个字的故事写在手心里,一笔一画,就是你和我的名字了。
红烛在来的路上燃尽了,回到剑阁的时候已经是深夜,陵越亲自在小炉上烧了热水,将折起来的青缎屏风再拉开几扇,和屠苏隔了一道屏风,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说的久了,屠苏那边渐渐浅了声音,转成绵长吐息,陵越这才收拾了桌上的书卷,磨了粉彩,铺开一张纸。
他想画幅蔷薇。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几声,他忽然凝了神,一滴朱砂从笔端坠下来,像眼泪一样,掉了下来。
屏风后突然传来屠苏低低的声音。
“师兄,很晚了,睡吧。”
“好。”
他轻轻叹了口气,放下了笔。
那年清明,夜里,陵越私自带着屠苏下了山,走的很急,将春水杜鹃染过的红绫松松往屠苏发上一系,就当是梳过了头。
阁门空响,屠苏回过头去,小灯摇曳,桌案上半摊开一卷书札,墨迹未干,那是清晨陵越才抄录完的经书,他念一句,屠苏就跟着念一句,圣贤断绝五色声香味触法,坐看须弥日月,六道无常。
清明时节,人间已是春气芳菲,天墉城位于昆仑山绝顶,七十二峰,积雪终年不化,坐在屋檐下时,便能听到流转其间的呜呜风声,清冷寒意缭绕眉睫。这样的天气,无怪屠苏偷偷养的一盆蔷薇冻伤了。如今本该是花期,乌瓷花盆里的花枝花叶可怜兮兮的蜷缩起来,屠苏看见了也没有说什么,只默默的把盆中枯萎凋败的春色连根拔起,丢进了后院的小潭。陵越这才想起,屈指算来,屠苏从他来时,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天墉城了。
没来由的,他想带屠苏去看一回清明雨里的蔷薇花。就算是圆满了他一场花开的愿景。
“师兄就不怕掌教和师尊责怪。”
屠苏不自觉握紧了陵越的手,脚步轻快了起来。
“若我被责罚了,屠苏也要罚。”陵越微扬起了唇角,“罚你去剑阁,端茶倒水。”
陵越说罢,屠苏许久没有回答他,陵越只以为他当了真,正要回过头去和屠苏解释,却望见屠苏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开了口,“我替师兄多带几束蔷薇回去,掌和师尊见了喜欢,就不罚了。”
“你怎知掌教和师尊喜欢花儿?”陵越失笑。
屠苏抿了抿唇,乌黑睫羽扑簌一闪,“我猜的。”
去时还有月亮,一步一步往山下去,暖意也随着一步一步萦绕上来,渐见了街市烟火,一条清清小河,弯弯曲曲往远方流去,月亮的倒影上落着几穗青青的柳花。两岸张着仕女的游春锦帐,浅碧绛红,水面泊着莲灯,光芒星星点点忽远忽近,却不知去何处才能看见蔷薇,陵越住了脚步,对屠苏道。
“我去问路。”
屠苏望着师兄,点了点头,立在河岸边。
陵越的身影渐渐去远了,屠苏收回目光,一盏灯被对岸人送到面前,风一吹,又转了一个弯,重重叠叠的花心里放着一张手掌大小的红笺,红笺上依稀有字迹,屠苏想看看纸上写的究竟是什么,而花灯越飘越远,终究是看不见了,他只得再立回河岸边,这片刻,他不知是更想师兄了,还是更不想了。陵越一会就回来了,想是问清了看花的路,他手里却多了一只红烛,红烛上系着一根点缀金粟长长的鸳鸯绣带。屠苏望他,陵越弓起手指,抵在鼻翼下轻咳了一声,“那边鹅黄罗帐后的姑娘跟我讲,能看花的地方,不曾有灯。”片刻他又补了一句。
“红烛是猜谜得的。”
屠苏伸手将垂落到地上的绣带挽起来,风将鸳鸯,缠绕在指尖。他抬起头来看他。
“什么谜。”
远处鹅黄罗帐外,有藕丝柳裙飘扬,往陵越屠苏二人这边看,素绢小罗扇一摇一摆。
“戍边走千里,草下有鱼禾。”
“师兄没有猜出来。”陵越向他道,“姑娘便嫌师兄笨,可怜师兄,就送了支红烛。”
屠苏听的愣了,心念一动,望向陵越。
陵越没有看他,将红烛收在袖里,“走吧。”
隔岸铃鼓踏摇,绣带上的鸳鸯又坠落在衣角。
只是陵越手里的红烛还是没能点亮来看花,他们来的太晚,小园已上了锁,门前寂静无人。陵越陪着屠苏在门前站了一会,才说,走吧。
清明节的蔷薇终究是没能看见,来时的河岸人也走尽,落花和烟火散落了一地,屠苏随着陵越走过生满青青郁草的岸上,突然记起来陵越去取红烛时,他自己一个人站在河堤,在水里看见的那盏莲灯,莲灯的花心放了一张红笺,如今,灯已经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但是屠苏仍旧想知道,那张红笺上写的字。
“戍边走千里,草下有鱼禾。”
他又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将目光落在烟月摇曳的河上,只当是那张红笺上,写的就是这十个字。
说的是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个人去遥远的边关驻守,边关离他的家有一千里,他走的时候,还记得小小妻子站在水田边,青青禾草间还有小小的红色鱼儿在游荡。
有过了很久很久,他走了一千里又回到了家,青青的禾草间,红色的鱼儿还在游来游去。
那个人记得小小的妻子和红鱼儿,小小的妻子和红鱼儿也记得他,都一起在等他回来。
我也记得你,把这十个字的故事写在手心里,一笔一画,就是你和我的名字了。
红烛在来的路上燃尽了,回到剑阁的时候已经是深夜,陵越亲自在小炉上烧了热水,将折起来的青缎屏风再拉开几扇,和屠苏隔了一道屏风,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说的久了,屠苏那边渐渐浅了声音,转成绵长吐息,陵越这才收拾了桌上的书卷,磨了粉彩,铺开一张纸。
他想画幅蔷薇。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几声,他忽然凝了神,一滴朱砂从笔端坠下来,像眼泪一样,掉了下来。
屏风后突然传来屠苏低低的声音。
“师兄,很晚了,睡吧。”
“好。”
他轻轻叹了口气,放下了笔。



 E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