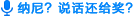◇◇
严郎入了诏狱,我疯了似的把那些锦缎衣服、狐皮貂裘,把那些恩客送的珠宝首饰卷起,统统当做了银票。惟独那个装着他笔迹的匣子,却碰都未敢再碰一下。
我耳边环绕着他的话音,我抖着手写信,我恍惚看见他站在屋角,眼睛闪亮的如同星子。
他对着我笑,说已经攒够了为我赎身的银两,绿水青山,天下无涯。我笑着说好,眼泪滚烫的烙在脸上。
我唯一的光,在黑暗里奄奄一息的光,这光可用我的性命交换,否则这性命又有何意义。
◇◇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不管是皇帝抑或九千岁,总都逃不过劫数。一发动全身,入了这网中,怎样都错。
魏阉一案,生死一线,只是沈炼没想到周妙彤会在这时来找他。
每一回她见到他,喉咙里都翻涌着生涩的腥。心里的伤口重被扯开,连脚底都发软,她却站定了,把信和银票给他。她的所有家身,只为救自己爱的人。
她依旧是一身常穿的素色衣服,斗笠上的纱遮住了一点苍白的脸。她下意识地咬了一点嘴唇,只有眼眶是红的。
他看着她,似乎有些怔住了。
他想带她走,带她去苏州,一间小院子,乌瓦青砖。
上穷碧落下黄泉,即便现在已是时间紧逼,刀刃迫在喉下,他仍未变过。
可还来得及。
“诏狱可不是随便就能出来。”
她叫他沈大人,一生仅此一次求他。
他刀刻一般的侧脸,霜雪凝在眼瞳里,融化成苦涩的盐。
她心间的最后一线火光,灌进那条裂隙里,疼痛撕裂了胸膛,烧尽心肺。
“你救了他,我就跟你走。”
沈炼在狱中见到了严俊斌,大刑逼供,血迹斑斑筋脉尽断。一身官服的锦衣卫支走了狱卒,把犯人解下来。
那扇门扉之外的背影,还有封在院落里的刀影。
他认出了严家公子,他欠了他的一只手。
“是妙彤让我来的,她带了信给你。”
曾经光明磊落的堂堂君子仿佛一只软弱无力的木偶,他勉强才能扯动嘴角。笑的仿佛嘲讽,
“我看不见了。”
药盲了的双目,乌云雾气遮蔽了漫天星辉,幽暗混沌之下便再没有路。
“只能请你,读给我听。”
锦衣卫附身在罪臣的旁侧,慢慢念出伊人写来的信。
她说要等他,等他的绿草依依,一生约定。
心间可翻涌如墨,寥寥数字,却字字都如钢针刺入胸膛。
一个废人该如何履约,他只求一死,以手换命,互不相欠。
何时杀人取命有过犹豫,颈骨在沈炼怀里发出折断的轻响,却让他仿佛一瞬间恍惚。
◇◇
我坐在暖香阁的房里,鲜红衣袍好像新嫁娘,等沈炼的消息。
他来找我,此刻此时给我赎身脱籍。
我暮然站立,我还来不及想象严郎在狱里受尽何等的折磨,来不及或是根本不敢。金屋华厦,锦缎珍馐,还有朱红窗框外的自由世界,不过如流沙般跌散。
他说我深爱的人死了。
他带话给我,只有一句。
不要再等了。
心血养着的一捧火,终于还是湮灭。微弱的最后的光,像打乱的萤火一点点仓皇消亡在浓厚的黑暗里。
一时间眼盲心空,耳边嗡鸣,四周只白茫茫一片。
沈炼在讲什么,也全慢慢听不真切。
或许是锦衣卫的奉命杀人,或许是斩了严家少爷的一只手,或许是乌瓦青砖的一间小院。
眼泪,我努力忍住的眼泪,不知是不是已经落下,冰凉或是滚烫,只是未有时间抽泣。
我的声音如同自遥远的天边传来,
“你以为我喜欢你,我只是怕你。”
我怕,手脚冰冷,浑身战抖。
而抱紧温暖我的人,再不会有。
那身玄色的飞鱼服仿佛永不散去的乌云压在我的心上。
他终于还是穿着它。
他是锦衣卫,带走我的亲人,杀死我的爱人。
他无数次在暖香阁房间里的沉默无言,他独自一人闯了诏狱,他说要给我赎身。
他是倾颓大厦之中的一颗细小铆钉。
他满是剑茧的手忽而拉过我,窗外的飞矢如雨,他带我辗转躲闪。
仿佛是丧失了一切的感官,时间变得漫长无边。烛火里他的脸是不是也充溢了悲哀,我不知道。
究竟是疼痛已密布了身体,还是只剩下麻木的冰凉一片。背后湿淋淋的是箭伤流下的血,或许这伤能让我死在这里,倒也是件好事。
他以一敌众,好像一柄漆黑的弓。
◇◇
她坐在屋口,门廊里依旧灯火通明,血渗透了红绸的衣服,艳丽的颜色混在一处,分辨不清。
她脸色苍白的像纸,仿佛丧失了魂魄。
门廊里躺满尸身,灯笼拉长浓重的黑影,他刀刃上一片粘稠滴落。
银枪长刀,金鸣相撞。
那廊下的一袭殷红,是他唯一的弱点。
◇◇
拿枪的人我并不认得,许是要杀了我,不过让死亡来得快些。
漫长的时间凝成一刻,灯辉晃动,浓重的腥味冲进胸口,心口里早已溢满的那些、翻涌的那些,都凝固了,再崩塌破碎、零落有声。
隔绝我的纱幕忽而全然落下,这孤零零的绝望世间偏要硬拉我回来,再逃之不得。嘈杂纷乱的声音蜂拥而至,呼吸声穿透我的耳膜。
沈炼,挡在我面前,锋利的枪尖刺进他的肩头。
◇◇
地上片片污秽血渍,四处死一般寂静无声。
锦衣卫刀下或许从无活口。他摇晃着走过来,依旧不发一言。
他在她身边蹲下,让她的手臂轻轻搭上肩头,将她抱起来。她没有闪躲,她的眼睛就像深涧寒潭,看进他漆黑的瞳孔里。
仿佛能看穿了他。
屋外下起了雪,初雪落在还未凋零的树叶,给青色上镀了一层寒凉的霜。
他背着她,踏在地上,血红雪白,一步一步都沉重的如同誓约。伤口是不是能被冻结,他的衣摆融进了夜色,她的红衣沾染了霜雪泥泞。他温热的血从她的指缝间滑落,她抬头望见苍穹如泼墨,不见了长庚星,仿佛有浓郁的槐花腥香气味卡在胸口里。
“若不是我,你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暗夜微光,雪终于遮盖了一切,那条路长的几乎没有尽头。
FIN.
严郎入了诏狱,我疯了似的把那些锦缎衣服、狐皮貂裘,把那些恩客送的珠宝首饰卷起,统统当做了银票。惟独那个装着他笔迹的匣子,却碰都未敢再碰一下。
我耳边环绕着他的话音,我抖着手写信,我恍惚看见他站在屋角,眼睛闪亮的如同星子。
他对着我笑,说已经攒够了为我赎身的银两,绿水青山,天下无涯。我笑着说好,眼泪滚烫的烙在脸上。
我唯一的光,在黑暗里奄奄一息的光,这光可用我的性命交换,否则这性命又有何意义。
◇◇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不管是皇帝抑或九千岁,总都逃不过劫数。一发动全身,入了这网中,怎样都错。
魏阉一案,生死一线,只是沈炼没想到周妙彤会在这时来找他。
每一回她见到他,喉咙里都翻涌着生涩的腥。心里的伤口重被扯开,连脚底都发软,她却站定了,把信和银票给他。她的所有家身,只为救自己爱的人。
她依旧是一身常穿的素色衣服,斗笠上的纱遮住了一点苍白的脸。她下意识地咬了一点嘴唇,只有眼眶是红的。
他看着她,似乎有些怔住了。
他想带她走,带她去苏州,一间小院子,乌瓦青砖。
上穷碧落下黄泉,即便现在已是时间紧逼,刀刃迫在喉下,他仍未变过。
可还来得及。
“诏狱可不是随便就能出来。”
她叫他沈大人,一生仅此一次求他。
他刀刻一般的侧脸,霜雪凝在眼瞳里,融化成苦涩的盐。
她心间的最后一线火光,灌进那条裂隙里,疼痛撕裂了胸膛,烧尽心肺。
“你救了他,我就跟你走。”
沈炼在狱中见到了严俊斌,大刑逼供,血迹斑斑筋脉尽断。一身官服的锦衣卫支走了狱卒,把犯人解下来。
那扇门扉之外的背影,还有封在院落里的刀影。
他认出了严家公子,他欠了他的一只手。
“是妙彤让我来的,她带了信给你。”
曾经光明磊落的堂堂君子仿佛一只软弱无力的木偶,他勉强才能扯动嘴角。笑的仿佛嘲讽,
“我看不见了。”
药盲了的双目,乌云雾气遮蔽了漫天星辉,幽暗混沌之下便再没有路。
“只能请你,读给我听。”
锦衣卫附身在罪臣的旁侧,慢慢念出伊人写来的信。
她说要等他,等他的绿草依依,一生约定。
心间可翻涌如墨,寥寥数字,却字字都如钢针刺入胸膛。
一个废人该如何履约,他只求一死,以手换命,互不相欠。
何时杀人取命有过犹豫,颈骨在沈炼怀里发出折断的轻响,却让他仿佛一瞬间恍惚。
◇◇
我坐在暖香阁的房里,鲜红衣袍好像新嫁娘,等沈炼的消息。
他来找我,此刻此时给我赎身脱籍。
我暮然站立,我还来不及想象严郎在狱里受尽何等的折磨,来不及或是根本不敢。金屋华厦,锦缎珍馐,还有朱红窗框外的自由世界,不过如流沙般跌散。
他说我深爱的人死了。
他带话给我,只有一句。
不要再等了。
心血养着的一捧火,终于还是湮灭。微弱的最后的光,像打乱的萤火一点点仓皇消亡在浓厚的黑暗里。
一时间眼盲心空,耳边嗡鸣,四周只白茫茫一片。
沈炼在讲什么,也全慢慢听不真切。
或许是锦衣卫的奉命杀人,或许是斩了严家少爷的一只手,或许是乌瓦青砖的一间小院。
眼泪,我努力忍住的眼泪,不知是不是已经落下,冰凉或是滚烫,只是未有时间抽泣。
我的声音如同自遥远的天边传来,
“你以为我喜欢你,我只是怕你。”
我怕,手脚冰冷,浑身战抖。
而抱紧温暖我的人,再不会有。
那身玄色的飞鱼服仿佛永不散去的乌云压在我的心上。
他终于还是穿着它。
他是锦衣卫,带走我的亲人,杀死我的爱人。
他无数次在暖香阁房间里的沉默无言,他独自一人闯了诏狱,他说要给我赎身。
他是倾颓大厦之中的一颗细小铆钉。
他满是剑茧的手忽而拉过我,窗外的飞矢如雨,他带我辗转躲闪。
仿佛是丧失了一切的感官,时间变得漫长无边。烛火里他的脸是不是也充溢了悲哀,我不知道。
究竟是疼痛已密布了身体,还是只剩下麻木的冰凉一片。背后湿淋淋的是箭伤流下的血,或许这伤能让我死在这里,倒也是件好事。
他以一敌众,好像一柄漆黑的弓。
◇◇
她坐在屋口,门廊里依旧灯火通明,血渗透了红绸的衣服,艳丽的颜色混在一处,分辨不清。
她脸色苍白的像纸,仿佛丧失了魂魄。
门廊里躺满尸身,灯笼拉长浓重的黑影,他刀刃上一片粘稠滴落。
银枪长刀,金鸣相撞。
那廊下的一袭殷红,是他唯一的弱点。
◇◇
拿枪的人我并不认得,许是要杀了我,不过让死亡来得快些。
漫长的时间凝成一刻,灯辉晃动,浓重的腥味冲进胸口,心口里早已溢满的那些、翻涌的那些,都凝固了,再崩塌破碎、零落有声。
隔绝我的纱幕忽而全然落下,这孤零零的绝望世间偏要硬拉我回来,再逃之不得。嘈杂纷乱的声音蜂拥而至,呼吸声穿透我的耳膜。
沈炼,挡在我面前,锋利的枪尖刺进他的肩头。
◇◇
地上片片污秽血渍,四处死一般寂静无声。
锦衣卫刀下或许从无活口。他摇晃着走过来,依旧不发一言。
他在她身边蹲下,让她的手臂轻轻搭上肩头,将她抱起来。她没有闪躲,她的眼睛就像深涧寒潭,看进他漆黑的瞳孔里。
仿佛能看穿了他。
屋外下起了雪,初雪落在还未凋零的树叶,给青色上镀了一层寒凉的霜。
他背着她,踏在地上,血红雪白,一步一步都沉重的如同誓约。伤口是不是能被冻结,他的衣摆融进了夜色,她的红衣沾染了霜雪泥泞。他温热的血从她的指缝间滑落,她抬头望见苍穹如泼墨,不见了长庚星,仿佛有浓郁的槐花腥香气味卡在胸口里。
“若不是我,你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暗夜微光,雪终于遮盖了一切,那条路长的几乎没有尽头。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