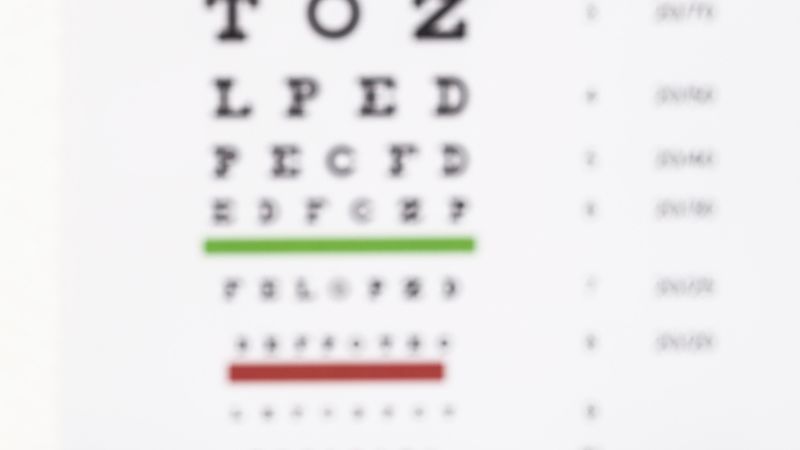我一直觉着在这个污染严重的城市,抬头看天空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我始终以为它的天空会是阴霾的,蒙尘的。跟那时的我一样,眼里没有希望,自然看不到风景。
一个人的失眠,原是两个人的画面。所以开始害怕无所事事,开始害怕休憩,开始害怕怀恋。我本来觉得逃得越远就越好,或许我就不会难过了,也不会失眠了。
到达部队的第二天,被很荣幸的请到隔离室,黑暗的地下室,一个人的空间。人们相信眼前的事物,能看见好过一切,所以也怕黑暗。可黑暗中,往往越发看得更清楚,因为你想用可以找到的一切东西,逃出这个牢笼。所以,看到的会别人更细致,更深刻。除了一颗图钉,两根烟头,我什么都没发现,就开始放弃抵抗。
无声的空间,无尽的遐想,很容易把人折磨疯。唯一能做的事,只有躺在床上,盯着十厘米的采光窗。
一个人的失眠,原是两个人的画面。所以开始害怕无所事事,开始害怕休憩,开始害怕怀恋。我本来觉得逃得越远就越好,或许我就不会难过了,也不会失眠了。
到达部队的第二天,被很荣幸的请到隔离室,黑暗的地下室,一个人的空间。人们相信眼前的事物,能看见好过一切,所以也怕黑暗。可黑暗中,往往越发看得更清楚,因为你想用可以找到的一切东西,逃出这个牢笼。所以,看到的会别人更细致,更深刻。除了一颗图钉,两根烟头,我什么都没发现,就开始放弃抵抗。
无声的空间,无尽的遐想,很容易把人折磨疯。唯一能做的事,只有躺在床上,盯着十厘米的采光窗。